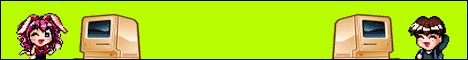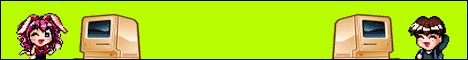杭州仁爱托管中心是浙江省第一家“民营公助”的仁爱托管中心。仁爱托管中心专门接收16周岁至45周岁中轻度智力残疾人及病情已稳定的精神残疾患者,通过对他们进行康复性训练,状况好的残疾人可以重新融入社会生活,而更多无法复原的残疾人则在这里找到一个可以托管终身、不受歧视的世外桃源。
仁爱托管中心座落在杭州东面的彭埠镇,它虽然位于闹市区,却闹中取静,院内绿树环绕,庭院错落,环境十分幽雅。在这里,智能训练室、电脑房、健身房、康复治疗室等各项设施一应俱全。
托管中心里的工作人员主要是杭州市智力残疾亲友会的成员,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照顾残疾亲人的切身感受,让他们对待每一位托管中心的学员,都像对待自己家人般亲切。
邵老师、许老师、徐老师……在托管中心,记者见到了这些善良的人们,在他们灿烂的笑容背后暗藏着一个比一个辛酸的故事。
听他们讲着往事,记者不禁想起一段曾在网上广为流传的话: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有一种力量,正从你的指尖悄悄袭来,有一种关怀,正从你的眼中轻轻放出。
中心的负责人邵老师告诉记者:“建这个托管中心,不仅是在帮助我们自己,更是想帮助那些和我们有着相同经历的人们。”
两个沉重的故事
故事一许阿姨的最后期盼
儿子刚出生时,一双大眼睛就会溜溜地跟着人影转;和他比划比划动作,他好像看得懂,眼睛笑成一条缝。那时侯,抱过他的叔叔阿姨们都夸他是个“聪明仔”。
1959年,我和爱人都还在部队工作,为了照顾这个小孩,我们每月从工资中抽出相当大一笔数目,请了个专职的阿姨。儿子2岁的时候,已经认得30多个方块字,我第一次体会到为人父母的幸福感和自豪感。
儿子3岁那年,我们从长春转到重庆,阿姨没跟来,我们只好把他放到托儿所,到了周末才接他回家。有一次托儿所的阿姨告诉我,小孩这一周发高烧,幼儿园的医生说儿子得的是腮腺炎,不要紧的,于是我们也没在意。
可是之后他开始表现出一些失常的举动:到处乱跑,有时候甚至跑到垃圾桶边上大呼大叫;看到邻居家开着门,就径自跑到人家的床上躺着不动……儿子还小,很多时候,我们也分不清,他是真的脑袋有问题,还是和我们瞎胡闹。而之后医院的检查报告彻底打破了我们所剩无几的“自我安慰”。
“是我们对不起他,孩子是无辜的。”我深深地自责,我不能让儿子的一辈子就这么没了,对孩子的那份沉甸甸的爱和责任感,让我们家开始长达几十年的求医苦旅。
别人说劳动可以启发儿子的心智,我就把儿子放到乡下,让他每天跟着干农活,可是回家后,儿子智力没增进,却学了满口的样板戏;有人说针灸对治疗有帮助,我就天天带他去扎针。小娃疼的掉眼泪,我也陪在一边哭;从报纸上看到“中药加鸡蛋”是帖好药,我每天炖给他吃,一个月下来丝毫不见起效;听说河南有个医生懂得以毒攻毒的治疗方法,我请长假带着儿子去看病,游医治到最后,把儿子搞成营养不良,轻度贫血……
为了儿子,我们夫妻彻底牺牲了个人的生活和爱好,我更是没什么乐趣可言。这么多年来,我们夫妻俩几乎没有共同在公开场合出现过,总要牺牲一个人留在家里照顾儿子。期间有一回托给人照顾,儿子乱咬东西,引发口腔炎症,此后我再也不敢让别人来照顾他了。
1987年,我和爱人调到杭州工作。这时儿子也长成大小伙,一米七几的个,模样还挺帅。我们把他寄放在社区办的工疗站里,每天做着拆回丝(记者注:一种手工活)的活,儿子的指甲磨平了,手指长出老茧。我虽然心疼,却再次体会到久违的幸福感觉:儿子像个正常人那样在劳动了。
工疗站里其他的病人每天都自己来回。儿子也如此。但有一次在他自己回来的路上,出了车祸。那辆车把儿子撞出三米高,当时我们都以为他没救了。没想到,儿子还挺命大。
出院的时候我含着眼泪告诉自己:儿子大难不死会有后福的。
带着孩子的40年里,我不止一次地想到:我是最苦的一个人,不如和儿子一起死了算了。可是看着他一个人静静地玩着,是那么乖;他一声声喊着妈妈,充满依赖;他也会在我和爱人吵架的时候,站出来帮我说话“爸爸不好,妈妈不生气”……
而且我永远不会忘记在那个下雨的傍晚,当我披头散发、全身湿透、像疯了一样四处找寻晚归的儿子,却看见他无助地站在工交车站里躲雨,身上不停地颤抖。我突然意识到:什么“想和儿子一起去死”、“不再管他了”都只是意气话,除了父母,我的儿子在这个世上,再没有人可以依靠,做妈妈的怎么忍心抛弃他?这辈子,我和我这个残疾儿子是绑在一起,无论如何也分不开。
前段时间,一个老同事的猝死让我感到震惊,他是死于心机梗塞,走的时候没留下一句话。从他的身上我想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今年已经67了,爱人也有70了,说不定哪天我们俩撒手走了,儿子的下半辈子怎么办?
虽然我们还有一个小儿子,但这几十年里,我们亏欠这个儿子的更多,我不想增加他的负担,而工疗站也不能照顾残疾儿子终身。
2000年,我加入亲友会。在这里,我认识许多和我有相同或类似经历的人们,共同的苦难把我们的心紧紧连在一起。为了我们所爱的残疾亲人,今年,我们共同创办了智力和精神残疾患者的托管中心。
当我带着残疾儿子走入中心时,感觉像回到了家。在这里,他是学生,我是老师,我们有各自的岗位和角色,生活得充实自在;在这里,我不用再担心世俗的眼光会伤害到我们母子;而更重要的是,在这里,我替儿子找了一个可以让他活到60岁的地方。
让他活到60岁,是我们夫妻俩对这个灾难重生的儿子最后的期盼和承诺。
故事二小贝的两个妈妈
托管中心的徐老师也有一个残疾儿子,平时这孩子都是姥姥带的。面对我们提出的采访要求,徐老师迟疑了一会,说要先打个电话征求妈妈的意见,对于这个孩子,没有人比胡妈妈更有发言权。
胡妈妈在电话里对于采访推辞了一阵,终于禁不住我们的请求,答应了。路上,我们了解到,这两天胡妈妈一直在生病,而我们打电话过去的时候,她还在卧床休息。我们不禁为自己的莽撞感到后悔。
胡妈妈的家位于武林门附近的一幢老房子里。阴暗的走廊、陡峭的楼梯,上楼的时候,我不禁想到“一个老人和一个小脑偏瘫并伴有癫痫症的残疾人走这样的楼梯是多么危险的事情”。
胡妈妈的房子在三楼。我们按了许久的门铃,才听到屋里有走动声,徐老师在门外叮嘱了一句“走慢点,我们不急”。
胡妈妈是一位气质非常好的老人,虽然她现在已是满头银发,但可以看得出年青时候她一定是个美人。
胡妈妈一瘸一拐地请我们进了屋,她歉意地说,上了年纪的人腿脚不利索,让我们在门外久等了。
在卧房里,我们见到了采访的主人公??小贝,他正低着头坐在靠墙的沙发上,他似乎对我们的到来感到局促不安。而直接铺在地上的床铺也引起我们注意。胡妈妈笑着说:昨晚小贝的癫痫发作,把床都摔坏了,现在我们祖孙俩只好学日本人,睡榻榻米。
谈到小贝,胡妈妈的话匣子打开了。小贝一生下来就是小脑偏瘫,那时侯,徐老师的爱人还在部队上,徐老师又是单位的业务骨干,根本没工夫照料孩子。于是胡妈妈把孩子带在了身边。照顾时间长了,交还给孩子的父母她还不放心,有一次凌晨2点了她还跑去把孩子带回来。
小贝是个残疾孩子,他的右半边肢体基本上不受控制,到了7岁才学会站立。可是12岁那年一次意外跌倒,让小贝又添了一样毛病——癫痫症。
每当小贝癫痫症发作的时候,胡妈妈就用双臂紧紧抱住他,尽量不让他东倒西歪,弄伤了自己,而最后往往被砸到的都是胡妈妈自己。现在,小贝长成24岁的大小伙,力气也大了,一发病的时候,胡妈妈渐渐控制不住他,家里的茶几、大衣橱镜不知被他打碎多少回。所以以往每天都去花园散步的习惯,这两年不再继续了,胡妈妈说:“他如果在外面发病,我真管都管不牢。”
小贝癫痫症发作一般有迹象可寻,譬如说他受到外界的声音、图像等刺激就会发病,而那之前,只要胡妈妈蒙住他的眼睛和耳朵,他慢慢便能平静下来。
多年来,为了治疗小贝的病,胡妈妈摸索了一套自己的办法。一到冬天,她就每天准备两大盆热水,把小贝的双手双脚都浸泡起来,或者给他煮人参吃。这些办法渐渐有了起效,小贝这两年犯病犯得少多了。
在照顾小贝之前,胡妈妈还有许多自己的兴趣爱好,可是在照顾小贝之后,她几乎没有个人时间。有一次,单位的老同事上家里串门,两老正聊得欢,另一边小贝却事情不断,不是上厕所,就是要东西。临走时,老同事悻悻地说:“你的外孙太烦了,以后不找你玩了。”胡妈妈的交际圈变得更狭窄了。
“为了这个外孙,我就这么老去。”胡妈妈摸着满头白发,颇有感触地说道。胡妈妈不止这么一个外孙,她却把大部分的爱都放在了小贝身上,家里人都对此表示充分的谅解。
“其实小贝也很懂事的。”胡妈妈说,“他爱琢磨家用电器,有时候还能帮我修修堵住的水龙头。他还爱剪报,剪了不少康复保健的内容,其中许多是关于老年保健的。我想,小贝是剪来给我看的……”
采访中,小贝的妈妈徐老师一直在旁边和儿子悄悄地说着话,给人的感觉,他们像姐弟多于像母子。我还记得她曾经告诉我,她的爱人在评价自己的时候说“这辈子做人没成功”,而那时候他才刚刚获得优秀工作者的称号。
徐老师或许和他爱人有一样的想法,尽管她嘴上没有说。他们夫妻俩面对这个残疾儿子都有相当大的精神压力。
徐老师辞掉了原先社区的工作,选择来到托管中心当一名普通的老师;她把孩子交给年迈的母亲照顾;她宁愿选择去照顾更多像她的儿子一样的残疾人,也不面对儿子……她应该是爱她孩子的,可能是她害怕面对残疾的儿子,那种亲情的绞痛让她无法承受。但她更无法舍弃这种感情,她从中生出了更深厚更广阔的感情,她把对儿子的爱和负疚一并给了托管中心里更多的残疾人。
在年初托管中心招人的时候,徐老师义无返顾地报名。
小贝是不幸,但又是幸福,他有两个好妈妈。
“我们晚上再过来修床,”临出门时,徐老师对她妈妈说,老人则是宽容地笑了笑。因为她明白,女儿现在又要赶回托管中心去,那里还有许多事在等着她做。
记者手记:
仁爱托管中心的创办代表着广大亲友会成员的一个普遍的心愿,它也代表着残疾人康复工作的一种新的模式,与政府财政拨款,街道派人管理的工疗站相比,托管中心是全新的“民办公助”形式。
而这种以收费为主要经济来源的方式,面对的是社会上最贫困、最需要帮助的群体,他们中有许多家庭为了治疗残疾的亲人,已经倾家荡产。他们非常迫切地希望能够把孩子送到托管中心来,但又无法承担每月600元左右的托管费。而一些境况较好的家庭,又担心孩子在托管中心吃不了苦,而任由孩子在家里慢慢退化。这些都确实让托管中心的创办者感到为难。
这项充满爱心的事业面临未卜的前途,采访中,创办者们充满着信心,但他们也不时流露出力不从心的无奈。他们渴望来自全社会的关爱,借着众人的臂膀来撑起这片不一样的天空。
如有热心读者愿意提供帮助,可拨打太阳星城爱心之旅热线:010?68392407 68392457,让我们来共同探讨如何更好的帮助身边这些不幸的人们。
(来源:《华夏时报》,作者:太阳星城爱心之旅特约记者池笑旖、特派记者王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