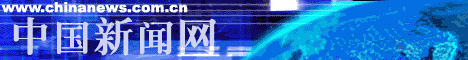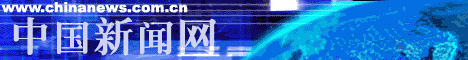°°°°ќ“‘шЊ≠ѕлєэ£ђЋ≠ƒ№≈™ґЃє≈іъ“ю њµƒ–ƒјнЄщЊЁЇЌ…ъіжЈљ љ°£∆д µ’в «√ї»Ћƒ№ §»ќµƒњќћв°£єэ»•ЇЌќіјі£ђґЉ“ї—щ£ђґЉ «≤їњ…ƒ№≈™ґЃµƒ°£
°°°°µЂ «£ђ÷–єъќƒїѓјп“‘»еЉ“ќ™ЇЋ–ƒµƒјн—ІіЂЌ≥÷–£ђ“ї÷±ґЉ∞йЋж„≈јѕ„ѓ—ІЋµµƒ«±––ЇЌ—”–ш£ђ’эѕс”–’в—щµƒ»ЋЊЌ±Ў»їіж‘Џƒ«—щµƒ»Ћ“ї—щЉтµ•£ђƒ«–©«еЄяµƒ»Ћ£ђиожс≤ї—±µƒ»Ћњ…ƒ№≤їЋµї∞£ђ‘Џјъ Ј…ѕ»іѕн”–ѕаµ±µƒќї÷√°£
°°°°ЈзЅчƒ—Ќ—ЇџЉ£
°°°°ќЇљъ ±Їт£ђ”–»Ћ‘Џ ЂјпЋµ£Ї°∞–°“ю“юЅкЁƒ£ђіу“ю“ю≥ѓ –°£°±’вјп£ђ°∞≥ѓ°± «÷Є„цєў£ђ°∞ –°± «÷Єљ÷ѕп°£њ…Љы£ђ»ќЇќ–ъѕщєƒ‘лµƒµЎЈљґЉњ…ƒ№≥Ѕµн„≈∆шґ®…сѕ–µƒ»Ћ£ђґЉ“їґ®Ѕф”–„ћ—ш«е—≈µƒµѓ–‘њ’Љд°£
°°°°ћ’‘®√чїЎЉ“ѕз≤…Њ’±їЇу»ЋЉ«„°£ђ «”–°ґћ“ї®‘іЉ«°Ј“їґќќƒ„÷Ѕфѕ¬јі£ђ√ї÷ш йЅҐЋµµƒ’≈ƒ≥јоƒ≥≤їЉыµ√√ї”–«е—≈єэћ“ї®‘іµƒµЎЈљ°£Ћщ“‘£ђќ“Ј≠Ќк°ґЇЃ…љ Ђ–£„Ґ°Ј£ђ–ієэ“ї∆™°ґЇЃ…љ–і Ђµƒјн”…°Ј£ђќ“ѕл£ђ й–і––ќ™ЇЌ“ю њ…ъ—ƒ «„‘ѕа√ђґ№£ђќ““‘ќ™’ж’эµƒ“ю’я“≤–нѕсЈз“ї—щ£ђ≤їЄш’в јљз„≈“їЋњЇџЉ££ђ’в÷÷ѕлЈ®”–µгњЅњћЅЋ°£
°°°°”…є≈÷Ѕљс£ђ»Ћ√«єЂ»ѕќЇљъ ±∆Џ «÷–єъјъ Ј…ѕ„ољ≤Јзє«–ю–йµƒƒкіъ°£ґ≈ƒЅ‘ЏЋыµƒ ЂјпЋµ°∞іуµ÷ƒѕ≥ѓљ‘њхіп£ђњ…ЅѓґЂљъ„оЈзЅч°±°£ќ“√«ЊЌјіњіњіґЂљъ£ђµ± ±µƒ√ы њЌхї’÷Ѓ‘Џіу—©љµЅўµƒ“єјп“ыЊ∆£ђЇц»їѕл∆р„‘ЉЇµƒ≈у”—іче”£ђЇц»їЄ–Њх“™Љ±«–µЎЉыµљіче”°£
°°°°Ќхї’÷ЃЅҐЉіґѓ…н£ђ√∞„≈—©£ђљ–…ѕ»Ћ≥Ћіђ≥ц––£ђ“ї÷±„яЋЃ¬ЈїЃіђµљћмЅЅ£ђ“—Њ≠јіµљіче”Љ“√≈њЏ£ђ»і„™…нЄжЋяЋЌЋыµƒіђЉ“µф„™іђЌЈ£ђЋыЋµ‘≠¬ЈЈµїЎ°£іђЉ“≤їљв£ђЌхї’÷ЃїЎірЋµ£Їќ“ «≥Ћ–Ћґшјі£ђѕ÷‘Џ–ЋЌЈ“—Њ°£ђќ“ѕлїЎ»•ЅЋ£ђЋ≠Ћµќ“Ј«“™Љыµљіче”≤≈„яƒЎ£њЇујі»ЋЋ’йш‘ЏЋыµƒ Ђјп£ђ∞—’вґќ÷ш√ыµƒ°∞—©“єЈ√іч°±љ–„ч°∞«е–ЋЈҐ°±£ђ«е—≈е–“£µƒ–Ћ÷¬ЇцґшЈҐ„ч”÷ЇцґшЌ£÷єЅЋ°£
°°°°≥ц ј‘љјі‘љЉиƒ—
°°°°°ґє≈ќƒєџ÷є°Ј÷–—°”√ЇЂ”ъµƒ°ґЋЌјо‘Єєй≈ћє≈–т°Ј£ђјо‘ЄЊЌ «ћ∆ ±Їт“їЄц÷–‘≠“ю њ°£ЇЂ”ъ–іќƒ’¬ЋЌЋыЈµїЎћЂ––…љ£ђƒ«„щ≤Ўµ√„°“ю њµƒ…љ‘ЏЇЂ”ъµƒ√и ц÷– «°∞»™Є ґшЌЅЈ £ђ≤ЁƒЊё®√ѓ°±°£
°°°°ґшґю Ѓ јЉЌƒ©£ђќ“»•ћЂ––…љ£ђ≈Љ»їµ«…ѕЇЂ”ъќƒ’¬јпћбµљµƒ≈ћє≈Ћ¬°£ќ“µ± ±њіµљµƒ «Ћ¬√н≤їєэ“їЄцє¬Ѕєµƒ–°Ќ§„”£ђ…љЌк»ЂєвЌЇ„≈£ђ‘ґі¶µƒ ѓћ≤µЎ…ѕ…Ґ≤Љ„≈ЌЏЊтїъµƒЄяЉ№„”°£ƒƒјп”– ≤√іјо‘Є£њћ÷¬џ“ю њ£ђєЎѕµµљµƒ≤ї÷є «јъ Ј£ђЄьґаµƒ «»Ћµƒїщ±Њ–ƒћђ£ђ“≤–н‘Џґю Ѓ јЉЌ„ц“їЄц“ю њ±»ћ∆≥ѓ£ђ±»ќЇљъ ±Їт£ђЄьЉ”Љиƒ—»±ѕ°ЇЌ«±“ю°£
°°°°Єя»Ћ“≤–ƒЉ±
°°°°ќ“њіµљµƒ“ю њµƒє ¬÷–£ђ”–ґЂљъ ±Їтљ––ї∞≤µƒ£ђЋы÷Єї”÷ЅєЎ÷Ў“™µƒд«ЋЃ÷Ѓ’љ£ђµ± ±√жЅўµƒ–ќ ∆ «µ–÷Џќ“є—£ђ’љЊ÷—ѕЊю£ђ„чќ™÷чЋІµƒ–ї∞≤£ђ“ї÷±∆љ–ƒЊ≤∆шЇЌ»Ћ‘Џ«е∆Іі¶ѕ¬ќІ∆е£ђ∆еЊ÷ґѕґѕ–ш–ш±ї’љ±®ітґѕ£ђќё¬џ ≤√і’љњц£ђЋы Љ÷’ґЉ‘Џ≤Љ…и∆е„”°£
°°°°µ»іт §ЅЋ’ћ£ђЋыµƒ∆е“≤ѕ¬ЌкЅЋ£ђ–ї∞≤їЎЉ“£ђљш√≈ ±Їтљ≈ѕ¬µƒƒЊем’џґѕЅЋ≥Ё£ђЋыЊ”»їЋњЇЅ√їЈҐЊх°£њ…Љы√ї”–»Ћїб≤їљф’≈£ђЋы“≤–ƒЉ±£ђ“≤«њ≥≈Њ÷√ж£ђ÷ї «Єя»Ћ“ю њ–ёЅґ≥цЅЋ≥ђєэ≥£»Ћµƒ’тґ®„‘»ф°£
°°°°°ґ јЋµ–¬”п.»ќµЃ°Ј÷–Ѕ–ЊўЅЋ≤ї…ўє≈»Ћ°∞»ќµЃ°±µƒ ¬јэ°£°∞»ќ°± «»ќ”…–‘„”„ч ¬£ђ°∞µЃ°± «їƒ√э°£і”є≈µљљс£ђґ‘”Џєэ”ЏЋж“вЈ≈јЋ–ќЇ°µƒѕыЉЂ»Ћ…ъґЉ”–Ј«“й£ђ°ґ—’ ѕЉ“—µ°Ј÷–≈ъ≤µљъ»ЋµƒЈзЄсЋµ°∞”ЎµЃЄ°ї™£ђ≤ї…ж јќп°±°£
°°°°µЂ «£ђ‘ЏќџƒаЈЇјƒјп≤ї»Њ£ђ‘ЏґсЋ„±йµЎ ±≤їєґЌђ£ђ«°«° «ќ“√«—џ«∞’в ±іъјп„оЄ√’дѕІµƒ°£
°°°°ќƒ’¬јі‘і£ЇѕгЄџ°ґќƒїг±®°Ј ќƒ/Ќх–°ƒ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