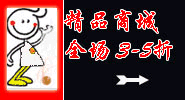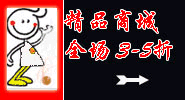-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温州商人在异国的经商之道仍然是个谜。皮包或餐馆,当年温州人靠这两样本事砸开了巴黎的地盘,成为可以独自挥舞上千万、上亿元个人资本的成功商人。但回头看看,温州人走的并非是一条牧歌式的迁徙之路,其中更有许多黑暗和孤独里的抗争。
-他们是中国内地最早的跨国商人,但似乎永远做着成功的小生意,鲜有庞大的集团公司。
-他们灵活地把工厂搬回国内,又率先发现了国内房地产开发机会。他们的未来方向在哪里呢?
从巴黎市内地铁线的东北角一站出来,走进一幢旧式楼房下面的大铁门,就进到一个传统的中国式车间,里面靠墙有一排缝纫机器,几个年轻女孩在上面娴熟地飞针走线。另外有几张大桌子,其他人有的在绑包装,有的在丈量皮包尺寸。
墙上有张白纸,用粗笔写着:发明生产工具,发明有效益的生产模式。
跟1980年代初所有来这里淘金的温州人所工作过的地方一样,这个皮包厂的设置、大小都没有变化。不同的是,几年前,随着大批温州人将皮包、服装制造厂从欧洲迁回中国,这种当年孕育了温州人发财梦的“摇篮”,如今在巴黎几乎找不到了。这间厂也多少有些时代标本的味道。
刚刚从国内回来的张女士是这家工厂的老板。她说这里的皮包生意很红火,定单太多,所以留下这个厂承担设计和一些紧急定单的处理。而自己设在浙江义乌的另一家皮包厂则包揽了大部分的生产任务。于张女士而言,内地是大工厂,而巴黎和欧洲国家成了大销售市场。在这种态势下,市场需求量不但没减少,反而有继续增加的势头。
除了自己的产品外,目前温州60%的轻工业产品尤其是服装,都由温州华侨引到了欧洲市场上来。
张女士此行还有件高兴事,就是她在温州附近郊区投资的房地产项目已经全面动工了,她说收益应该在两三年之内。
巴黎的亚洲新贵
谁也不知道,温州这个小小的城市究竟埋藏了什么神奇的能量。
温州人四处迁徙,把店铺开到全世界各地的故事早为人知。在巴黎市区或罗马火车站出口,你能看到成百上千家店铺绵延数十里驻扎着清一色的温州兵团。现代版成吉思汗传说在他们脚底下神奇地展开:攻城略地,无往不胜。仅巴黎地区,温州移民的数字就是15万。
如今到欧美旅游,你不会说英语没关系,能说温州话说不定比英语还管用。
在位于塞纳河边的巴黎市政厅,从它侧面一个明亮的路口拐进去,就到了“寺庙街”上。往里走,两边大小不一的中国橱窗里,挂满了颜色鲜艳的围巾、丝绸,那些身材不高、出来进去整理货品和招呼客人的温州人,神态平静、乡音入耳,让人很容易误以为到了浙江某个小镇的夜市上。
这条优雅而不事张扬的“寺庙街”,正是温州人在巴黎最早的据点。现任华侨华人会主席林加者,就是第一个把围巾店开上这条街的人。说起二十几年前的“寺庙街”,有着中法混血血统的林加者笑笑说:那时还完全是犹太人的地盘,我们只能拣人家扔掉的布头。然而,与一百年前初闯法国贩卖石品的浙江青田人、贩卖纸花的湖北天门人不同,1970年代初到来的这位林家第二代,却幸运地看到了比以往任何赴法“谋生”的移民都有利的形势:中法经贸关系的加强,浙江沿海一代新移民的增多。
于是林加者凑了钱,雇佣工人日夜不停地做工。自己则开起货车,跑遍里昂、马赛等所有城市,凭着在军队里摔打了一年的法语,推销产品。同时期,零零散散的其他温州店,也开始出现在这条街上。
有着商界老大身份的犹太人的地位开始动摇了,因为他们第一次面对做工不要命的温州人。温州人的苦干不唯什么主义和理论,练滴水穿石的功夫,这是任何商业字典里都找不到的路数。犹太人渐渐开始出卖店铺给温州人,后来温州货的畅销势不可挡,犹太人的店里居然也写上了中文。而今天,这条街已经名正言顺地归温州人管辖,犹太人选择了退出。
从“寺庙街”继续向东,穿过共和国广场,来到地铁美丽城一站。沿街铺天盖地的中国超市、餐馆、服装店、理发店招牌,看得人眼花缭乱。扎着围裙、奔跑着忙碌的温州人,甚至没有抬头跟你打个招呼的时间。当然,这条街的热闹还混杂着诸多不安定因素,它也是大批偷渡客、妓女、黑人、阿拉伯人的聚居地。但没关系,这些要么伸手向政府讨钱,要么生财另有其道之辈并不与温州人相干。
占领区并没结束,美丽城再往东,温州人的店已经火爆延伸至巴黎郊区93省。特别是近几年,这种神速扩展竟可制造一夜暴富的机会。3年前一家店铺卖50万法郎还没人要,现在它的价格飙升到55万欧元。有位戴先生于是把自己一间很大的仓库隔成很多间店铺出卖,几乎一夜之间就发了地主财。
除此以外,环巴黎市郊一个大圆的范围内,还分布着上千家温州餐馆。
上述正是目前巴黎的温州店铺图略。可以看到,眼下的温州拓展方式是带些霸气的。在巴黎11区,前不久就引发了当地区政府和老百姓的集体罢工抗议,原因是温州人以服装批发店垄断整个街区,造成生活不便。温州人把店铺从小路开到大路、小街开上大街,形成发散式集市。接着他们以高价买下周边所有的咖啡店、面包房、洗衣店等统统做服装批发,一个200平米的店铺卖到100万欧元的天价。然而,过惯了早上面包、下午咖啡生活的法国老太太们不干了:你们都卖衣服了,我们去哪里喝咖啡啊?
当然,协商以后,那里又有咖啡店重新开张了。
如今巴黎夜色里,商场的硝烟弥散之处,开着奔驰长龙、从容周旋于生意场和高档消费地的温州新贵们,俨然成了一支不可小觑的商业力量。他们住郊外的法式别墅、送孩子读私立学校、穿用名牌服饰、挤时间度一次奢侈的假期;他们早点仍然喝豆浆,仍然喜欢群聚并奔忙,却早已不是当年街头身无分文、四顾茫然的亚洲苦工,而是可以独自挥舞上千万、上亿元个人资本的成功商人。
为什么是温州人?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温州商人在异国的经商之道仍然是个谜。去欧洲的中国人非常多,但为什么偏偏是温州人如此成功?
强烈的赚钱欲望可能是温州人成功的第一要素。没有一个温州人试图掩饰他们血液里始终兴奋着的发财欲望。不赚钱,毋宁死。这是他们的逻辑。“我们温州人是青蛙,在水里会叫,在岸上会跳。”穿黑色唐装、有着北方人的高大身材和爽朗笑声的李建新这样说。1980年代初来法的温州人,身份各异:工人、会计、农民、手工业者、个体商人。那时几乎要借钱买机票的境况,注定了他们无一例外地要从皮包厂和餐馆的苦工做起。这是当时华人仅有的两档生意———规模不大,经营状况良好。
李建新也是从皮包厂做起的。开始不会用机器,从粘胶水开始学。到后来他做皮包速度之快,在巴黎同乡里都出了名。他说在老家5个兄弟住一间25平米的小房子的境遇必须要改变,邻居和同乡的致富他都看在眼里,既然参与了这场淘金之旅,自己绝不能落后。而原来会计出身、打算盘的陈先生,也学得一副绘图、剪裁的好身手。“我把自己当成囚徒,所以看不见巴黎的太阳也没关系。”李建新平淡地说道。朝九晚五的国内人是无法想象这个人群的艰辛。温州人跟人攀比、赚大钱的愿望太强烈了,“所有工人每天都是15个小时做工,那时想着比住监狱的人还有些自由,也就扛过去了。”李建新说,自己刚到巴黎时,有整整5年的时间没见过太阳,早晨天没亮开始做工,晚上上了法语课以后还要做工。他至今都记得那个场景:夜里12点多了,他拎着饭盒收工回家,常常与其他同乡在街头碰到,大家只是疲惫地互相点点头,然后擦肩而过。
温州人承认自己不比犹太人聪明,也没有与人家匹敌的经商史。但这个后来被称为“中国犹太人”的人群,却以吃尽天下苦的不二法则吓退了整条街上的犹太人,挤进巴黎商业场。
在所有人都有了小小的手艺和资金积累之后,温州人最乐于称道的群体团结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最初小老板的起步资金几乎不需要很久的积累,有人要开店,亲戚朋友都会解囊相助。李建新记得很清楚,自己最早开工厂时只有7万法郎的存款,五十几万的投资都是朋友们凑来的。慢慢赚了钱,他可以一月一万元的速度还回去。
随后,家庭作坊式的制作与经营节省了大笔的成本,使温州店的起步之路非常平稳。林加者曾指着一幢旧式楼房说,他一家人开始时租的就是那种最便宜的顶层小阁楼,20平米。一台机器每天转,再加一张桌子,晚上用来睡觉,白天用来做工。
与其他法国或犹太人的店不同,他们不会另请外人做会计或员工,所有管理都是夫妻俩或加上孩子来完成。正是基于这种需要,温州人的到来都是滚雪球似的,生意不断扩大,他们不断从家乡找来兄弟姐妹一起做,所以很多人出来的时候孑然一身,回乡探亲时已经是妻儿亲戚十几口人。他们起初甚至捡来犹太人扔掉的布头或碎皮,做成小钱包出售。同样一条皮带,别人卖15块,温州人卖12块。压低了成本和价格的货品,让他们的市场很快光亮起来。
在整个欧洲经济快速发展、皮包生意红火的时期,几乎所有温州皮包厂走的中低档产品的路子,都获利丰厚。那时普通收入的女顾客也要隔段时间换个新包用,这成了他们不间断的客源。1980年代末生意最好的时候,工厂的定单像雪片一样,早晨出了货,中午还有电话来催货。怕的倒是你没力气。
上个世纪后20年,中国内地还没有摆脱黑白灰的主要着装色调之时,时尚之都的巴黎却气象万千。敏感的温州人慢慢发现,其实财富的颜色跟潮流是统一的。
你要问温州人在开始就肯定自己能赚钱吗?当然摇头。陈武说生意本身就是场冒险,这个戴眼镜的潮流主义者的经验是:要敢为天下先。他请来犹太女设计师,还自创了一个叫“CHANON”的品牌,标志是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年轻女孩,他说这个理念是“自由世界”,很法国。
陈武与别人有点不同,他经常谈论的竟然是波德莱尔和兰波———法国人推崇备至的19世纪诗人。刚到法国时,父母不和睦曾使他陷入困境。他很快入了基督教,想从上帝给犹太人的原罪里,寻求救赎和忍耐。大概因为年轻和对命运的思考,他有了观察生活的兴趣。1985年他开第一家皮带厂的起点就是创造性的。当时法国市场只有香港、美国供应的传统式样的腰带,他却从展示会上巴黎女人姿态万千的衣裙上,想到了做装饰腰带。仍然是普通材料,仍然是自己开车全欧洲推销,就这样,1986年,在国内普通工资标准只有几十块钱的时候,他的店竟达到三四百万法郎的月营业额。
1991年,在另一次展示会上,他忽然发现中国的一种丝绸非常抢眼,KENZO等牌子的当季新款同时采用了这种自然、柔软的面料。他与一个国内刚刚来法的朋友短暂商议后,拿出1000法郎让他进来此面料,随后他把设计制作的产品带去荷兰、比利时、瑞士、德国等地。两年之后,他的店稳定在了每年1亿法郎的营业额。
温州人讲求“富贵”,所谓先富而后贵。温州特色不仅仅是苦打苦干,他们还要在潮流里面玩点儿品位。奔驰和名牌不代表真正的品位,这个品位,倘若你去陈先生的“禅”里坐坐才会感同身受。
“禅”是位于香榭丽舍、塞纳河、凯旋门包围中的一家投资千万元的中餐厅,这个号称金三角的所在是巴黎最贵的地段。一楼滴水清岩,木桌花草;二层镂空木窗、古董琴音,俨然把江南园林移步换景的精妙唯美搬来了法国。店命以“禅”名,又与佛教文化在欧洲的流行相得益彰,讲求修养、清净之道。这里除了川菜、温州菜、粤菜以外,还混合了许多法式料理的风格。去年底开张至今,这里接待的客人已包括摩纳哥王子、法国明星、部长要员,还有个陈老板一直记不住名字的英国某摇滚酷哥更是这里的常客。有趣的是,时常还有楼下的客人要求随着神秘的木头旋梯和悠扬古乐去楼上参观一下,法国人总是搞不懂,如此匠心独具的中国装饰到底是用哪根神经想出来的?
陈先生不掩得意之色:餐厅不能只讲吃,讲的还是品位。目前不到200万法郎的月营业额显然还只是开端,他对未来涨势毫不怀疑。他后来还知道,一个美食杂志的法国记者享用了他店里的美味以后,在FIGAROMAGAZINE(费加罗杂志)上悄悄做了一个整版的免费推介。
中国是新的发财梦
皮包或餐馆,当年温州人靠这两样本事砸开了巴黎的地盘。回头看看,温州人走的,并非是一条牧歌式的迁徙之路,其中更有许多黑暗和孤独里的抗争。他们可以随遇而安,没有很强的家园概念,但他们对成长过的地方有着始终的关注和信任。
在最初的餐馆或皮包生意里积累了一定资金的富裕温州人,开始考虑“钱生钱”的问题。而法国人对此则显得有点束手无策。法国是个多民族、人种混杂的地方,它是自由世界没错,人们可以在法律的边线内自由生活,但这个边线又足够严格。商业规则也是如此。
1990年代初,头疼的“黑工问题”曾使为数不少的温州人的生意遭受重创,严重的还要跟警察局纠缠数月之久。那时的温州工厂除了偷渡过来的既懂机器又说温州话的工人以外,根本不可能请到其他工人。这些人没有法国居留证,只能“黑”在厂里,无法报税。老板们惟一的选择也只是冒险。在温州街,人们还记得曾遭到过巴黎警察、税务、移民等部门的联合封街突袭检查,黑工、逃税的店铺要关门和重罚,有的店曾因此一次损失近千万元。还有面料成分与标签稍有不符,当即要销毁所有产品。一段时间,温州店主都如坐针毡。
加之银行系统对个人账户和资金问题的审查非常较真,以及高税收的政策,温州生意的继续上升之路,显得犹豫和谨慎。而1990年代,中国国内经济形势的好转,使海外温州人开始回国做生意。
1992年,在皮包生意里积累了大笔财富又因黑工问题跟警察局搞得心灰意冷的陈先生,就带着这里的经验和资金选择回杭州投资了。他在杭州做了一家皮包厂和化妆品厂,请朋友经营管理。
但事实却不如他想象的那么顺利。远在巴黎的他,并不了解国内当时正盛行的吃回扣风,直到有一次,他回国去买东西,售货员机械地问了句:发票开多少?他才恍然大悟,但为时已晚,两家厂的经营都十分平淡,加上自创品牌化妆品的宣传力度不够。几年以后,两家厂先后关门和转让。
如陈先生一样,早些年的温州人都零零散散地回国投资过一些项目,但收益微乎其微。而一部分经营景气的,也并没有能力带走赚来的资金。
1995年,国内出现了招商引资政策。中国内地大力支持欧洲知名侨会回国投资房地产事业。像华侨华人会这样的侨会首领们开始频繁到内地组织考察,同时,国内各地政府来欧洲考察的工作也互动起来。双方在交往和互访的过程中不断碰撞出商机。
温州人开始在最熟悉的温州本地投资房地产,他们先与政府机构合作,拿到土地开发权,然后建筑和出售房产。直到后来温州地价猛涨,以至一亩地涨到800万的天价。他们意识到,再投下去风险就不可测了,于是开始向其他省份拓展。
前几年,温州人在苏州有名的新加坡园区里搞出了温州园区,由温州人自己去招厂商入驻。这个集中了服装、鞋帽等所有服饰企业的园区很快形成了无所不包的服装城,方便所有客人的采购,且能以自己的工业带动产品销售,是个一石两鸟的好主意。
不久前,侨会的李先生等人在济南看好了那里“团购房”的巨大潜力,他们在经过合理的考察和预算之后,十几人合资近6亿,开发了市中心占地20万平米具欧美风格的“巴黎花园”。他们与房管部门合作,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内付清了土地款。目前,这个沿缓坡向上、具有极高绿化水准和强烈立体感设计的花园小区将全面进入施工阶段,李先生等资方对它未来的收益充满期待。
李先生说他们的下一个设想是要搞个汽车城。温州本身是个汽配基地,但温州地少,工业用地价格太高;同时大部分汽车工业在东北,运输便宜,山东正介于两地之间,如果能转移相当规模的温州汽配厂分厂到山东,未尝不是个好主意。
温州的服装和皮包厂大举“回国”也在最近几年形成热潮。内地工厂引进了先进的制作技术,成本大大低于他们在巴黎制作的消耗。他们在浙江、广东等地设厂,在巴黎销售,获利更丰。
未来是个简单的方向
“要既有文化又有钱,有品位,有分量,打个喷嚏都影响地球自转速度。”美国的一位温州商人对下一代如此期望。
北美人总是充满了挑战精神,欧洲却大不相同。住花园别墅、看艺术展长大的温州新新人类,大都吸纳了老欧洲优雅沉着的人文气息,他们强调个性的舒展和闲适的姿态,财富却退为某种模糊的概念:钱不必多,够用就行。眼看着店铺无人继续的父母们,对一心想着“打政府工”的下一代感到很无奈:谁让他们中了法国社会的毒!
但这其实是玩笑话,几十年没有周末假期、日夜工作的早期移民群,他们富裕之后的心态已经十分平静。他们不会真的要求孩子早早到店里来帮忙做老板:“只要他们愿意读书,念到哪里就供到哪里,重要的是尊重他们的选择。”
如今做超市生意的李建新会带着孩子们踢足球、学国语,但问到要不要儿子接老爸的班,他坚决地摇摇头:超市是我们这一代人做的,他们要读好书,温州人的下一代重要的是有学问和身份,很简单地生活。他还希望漂亮的小儿子以后回国当演员。
做了一辈子生意的温州人其实很有自知之明。他们被说成“中国犹太人”,在生意场上也的确表现出越来越强劲的上升态势,但他们知道,目前国内产品市场的强大支撑才是他们如此霸气的真正原因。而超常的低头苦干的精神让他们得以在竞争中胜出。
温州人并不真的具备与犹太人等同的力量。犹太人基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在科技和金融领域都有着最优秀的表现,他们的下一代选择做律师和医生的兴趣也是他们退出生意场的重要原因,他们的优势是可以贯通很多领域。
温州人的软肋是文化。陈先生提出个数字:在巴黎一年赚几百万容易,赚几千万就有难度。除环境因素以外,很多温州人都同时遇到继续上升的瓶颈:语言和交流问题。像“禅”这样的中餐厅挖来有30年行业水准的法国人做总经理的例子到底还是少数。有限的法语水平和在思想领域很少真正与法国社会沟通,制约了他们更大胆地尝试新领域。
温州人始终群居、温州生意总体上限于个体经营而少有集团化的状态,就可以说明些问题。而夏先生的西餐厅请了法国服务生没错,不满意想“炒”他们却很头疼,你要先后发出3封挂号信说明理由,喜欢讲逻辑的法国人还要讨出无数个说法,所以夏先生的官司到今天也还在打。
给非老板的普通温州人画像:生活单调、日夜做工、生活在巴黎气质之外。足够光鲜富有的老板们毕竟比例有限,而普通打工者才是温州人里基数最庞大的群体。
谁也不知道,温州人的小生意会做多久,也许他们的下一代会找到新的方向。(来源:南方都市报;作者:郭俏)
敬请关注:中新华人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