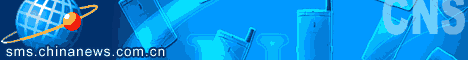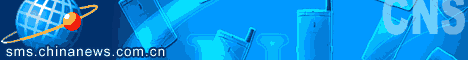在准备这个题目时,一直在思索,在我自己的生活里,到底“全球化”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我的早点,往往是牛奶、面包,涂奶油果酱。若是在国际的饭店里,你面临的选择,基本上不是欧式就是美式。边吃早点边读报。看你人在哪个城市,先读当地的报纸,可能是香港《明报》,可能是台北《中国时报》,可能是新加坡《联合早报〉或是《法兰克福汇报》,但是有几份国际的报纸是不管你在哪里都会找来看的,譬如《国际先驱论坛报》、《亚洲华尔街日报》,或者听BBC的广播,看CNN的电视报道。
用完早餐,进到浴室冲凉;洗发精的品牌——不管你是在北京还是香港台北纽约,大概都是同样那几个国际品牌。连卫生纸都是。坐在梳妆台前,发现你的化妆品,不管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角落,你用的品牌都是那几样:法国的、美国的、日本的……我是对名牌衣服没有感觉的人,如果讲究穿品牌服饰的话,那么衣橱一打开,入眼也是那几个熟悉的名字,法文、意大利文、英文。
连城市的样子都一致了
食跟衣是这样了,那么住、行、育、乐呢?
住,一个宜家的家具就把每一个公寓,不管是在墨西哥还是上海、是赫尔辛基还是洛杉矶,都“统一”了。出门坐车,别说是汽车就那几个固定的选择,连不同城市的地铁都是几个品牌公司的产品。别说家具、汽车等等商品已经全球统一,连城市的样子都一致了。所谓街道家具——马路边的路灯、公车站牌、广告设置、人行道设计等等,都变成了全球企业的产品。都市的景观和建筑,透过国际竞标,由少数全球化的建筑师与开发商运作,造成面貌相似的大城市。
食衣住行如此,育与乐就不一样吗?我在吃了欧式早点之后,开着德国品牌的汽车,驶过法国公司设计的街道,到了一个英国建筑师建造的美术馆大楼,去看一个新的当代艺术展。很可能是一个多媒体的影音展,用录像机、照相机所摄下的现代感十足的光怪陆离的人生影像。很有意思,但是如果这种展看多了——譬如你已经看过多次的意大利威尼斯展、巴西圣保罗展、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展、德国卡赛尔展、韩国光州展等等,你会有一个疑问:尽管艺术家不同、地理位置和国家文化不同,怎么“现代”的解释却大同小异、似曾相识?
看完展览之后,也许还有时间进了书店。这个书店一进门的地方大概就摆着《哈利·波特》,在香港和台北是繁体中文版,到北京和新加坡是简体中文版。如果是在马德里,会看到西班牙版。在柏林,会看到德文版。不管在哪里,不管什么文字,反正都是哈利·波特。
跟你到天涯海角
晚上,很可能去看个电影。要避开好莱坞的全球产品可不容易;《铁达尼号》或者奥斯卡印记的《卧虎藏龙》在马来西亚的乡下或是伦敦的市区里都看得见,有如麦当劳的标准菜单,“全球同步”。如果不想看电影,留在家里懒惰地看电视,会看到什么呢?我最近搬到香港,电视一打开,刚看见片头,孩子就说:“这个电视节目我知道。”同样的电视节目,美国制片的,在德国放映是德语,在西班牙放映是西班牙语,到了香港就是用粤语发音。人可以到天涯海角,全球统一了的食衣住行育乐跟着你到天涯海角。
睡不着吗?想吃一颗安眠药,你会发现,连安眠药也是全球一致的。头疼的吗?止痛药也是全球一致的。养鱼吗?你喂鱼的饲料来自一个国际连锁商。要快递东西到外国去吗?DHL或是Federal Express,不管你是在北京、台北、法兰克福,处理方法是一样的。发生了法律纠纷吗?需要人寿保险吗?国际连锁的律师事务所、全球连线的保险公司,正等在你门口。
不仅只是食衣住行的物质,还包括育乐的文化价值和观念,在全球化的运作下,都成为统一的商品,渗透了我的24小时,令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在100年前梁启超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谈所谓的“西学东渐”。西方的影响刚刚来到门口,人们要决定的是究竟我应该敞开门来,让它全部进来呢,还是只露出一条小小的缝,让某些东西一点点进来。在100年后的今天,所谓“西学”,已经不是一个“渐”不“渐”的问题,它已经从大门、窗子,地下水道,从门缝里头全面侵入,已经从纯粹的思想跟抽象的理论层次,深入到生活里头成为你呼吸的世界,渗透到最具体的生活内容跟细节之中了。
99%是西方的影响
然而什么是“全球化”呢?这个词其实是有问题的。影响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是什么力量在“转化”谁,谁被谁“化”掉啊?渗透到我的24小时生活细节里来的,难道是印度或埃及或阿拉伯的影响吗?不是的,仔细看这24小时的内容,代表“全球化”的东西中,其实99%是西方的影响,是西化。然后再细看西化的内容,譬如说讲物质的品牌而言吧,其中又有非常高的比例,是美国来的东西。所以对我们而言,所谓全球化的内涵高比例是一种“美化”的过程。
因为全球化其实挟带了大量的美国化,所以许多欧洲人对全球化也是戒慎恐惧的。激进者甚至于诉诸暴力,对他们认为象征全球化的符号——星巴克、元首高峰会议、麦当劳等等,进行抗争。人们所忧虑的,一方面是资源的垄断——韩国甚至有农民以自杀来凸显全球化所带来的本土产业问题;一方面是价值的垄断,因为价值被包装成为商品,随着跨国企业的操作,似乎威胁到本土文化的独特性和完整性。当德国的某一家报纸因为经营不善而可能被英国报业集团收购时,德国总理亲自出面斡旋,为的是不让外资进入本国文化的领域,报纸塑造舆论、传播价值,更是文化的敏感神经。
在我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对“全球化”第一次发生“戒心”是在1975年刚到美国时。在台湾读大学时,教英语的美国教师会要求每一个学生选一个英文名字,因为她可记不得几十个中文名字。于是一整班的学生都变成了Dick, Tom, Harry;我的名字叫Shirley。
难道不是文化的傲慢?
到了美国,我开始教美国学生英文写作。面对二三十个美国学生,很难记得谁是谁,我花了一整个下午的时间把人名和脸相配起来,认得了。于是我回想,为什么教我的老师没坐下来花时间,把我们的中文名字记住,反而让50个人都为她的方便而改名呢?
这难道不是文化的傲慢吗?有了这个认识之后,Shirley从此消失,被“Lung Yingtai”取代,而且不是“Yingtai Lung”。23岁的我觉得,你美国人可以学着发中国名字的音,你可以学着去记中国人的名字和他的脸,你也可以学着知道中国人是把姓放在名字前面的。1975年,我还没听过“全球化”这三个字,但是对于所谓文化“交流”事实上是“流”而不“交”的现象,已经觉得有点怀疑。
随着跨国企业的发展,文化是商品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我这一代几乎是看洋书长大的一代。当我去开国际笔会的时候,在这样一个各国作家汇集来谈国际和平与文化平权的场合里,我这读洋书长大的人就发现,你可以和大家谈莎士比亚、歌德、托马斯曼、海明威,但是你不能谈曹雪芹、庄子、韩非或张爱玲,因为,文化商品,大半是单向输出。
在法兰克福有一天我想买本德文版的《道德经》给孩子,走进当地最大的书店,到哲学部门,找不到;文学部门,找不到;政治学部门,找不到。最后在哪里找到呢?Esoterics(神秘学)!老庄孔子的书,和风水、日本化的禅宗、生肖、气功、太极拳放在一起,作为同类商品。
我们的书店会把柏拉图跟西洋占星术归为一类吗?不会,但是我们有可能把非洲最严肃的小说和非洲的“野兽大观”或者“食人族奇谭”放在一起。不是吗?
全球化是一个既让人欢迎又让人不安的现象。文化,还有人们安身立命的价值,都和商品一样一卡车一卡车卸货,直接送入家门。欢迎,因为我们突然多了选择,不管是洗衣粉的牌子还是政府的形态;不安,因为,这种选择往往是强迫性的——虽然我们或不感觉,只不过是强势推销的产品,不见得是对我们最好的;更因为,选择往往破坏了家里原有的秩序——伊拉克人究竟要不要欢迎美国士兵带进来的文化和价值呢?为什么要又为什么不呢?
这种不安对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是很熟悉的。我曾经遇见一名印度作家,谈起我们年轻时知识的启蒙过程,发现我们都是美国新闻处的“受惠者”。在那个物质与精神都匮乏的年代理,美国政府透过组织和金钱,有计划地将美国价值观全球输出。你说它不好吗?对于我们民主开放的追求,它是有重要贡献的;说它好吗,它又包藏着其他的目的,也限制了我们对未来的想像。
那么,对全球化的戒慎恐惧,和对国际化的追求,有没有矛盾?你不是一直呼吁要国际化吗,那么为什么对全球化又不是一心的拥抱?
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差别
国际化跟全球化两者之间有着非常关键的差别。全球化,在我的理解,是商品——包括物质和精神商品——的无远弗届;身处亚洲,我们往往是那“输入”的一端,备受影响,当然要无比的谨慎。国际化,是对于国际有深入的了解,掌握知识,从而发展出一种与国际沟通和接轨的能力。
当你进入香港的网页,你发现它用老练的英语、生动的画面、完整的资讯,很有效地让外人马上认识这个城市:它的历史、它的特点,哪里好玩好吃,哪里可以带孩子去。
当你进入台北的网页,障碍马上就出现:英语别扭,内容乾燥——应该是精彩的城市导游的地方,竟然是对观光者没有太大意义的政府组织结构。当你进入上海网站时,你发现,画面比台北活泼,设计也比台北对味,可是,一点进去,内容是空的。
进入香港机场,视线所及之处是精美的巨幅广告,活泼的英语告示,现代感十足的商店,完善的路线指标。进入台北机场,突然安静下来,好像到了“乡下”;英语少了,广告少了,指标少了。虽然整洁明亮,可是空旷寂寥。进入北京机场,就连“乡下”都不是了。墙上是空的,客人第一个看见的东西是高悬在海关头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条例”。
人们进入香港时,整个机场营造一种兴高彩烈的气氛告诉你,“香港是亚洲的世界之都,我们欢迎你”。进入文化最深厚的北京,劈面给你的第一印象却是冰冷森严的管制法令,犯了什么什么法的人会被递解出境云云。
用国际语言和手段“呈现”自己
就文化内涵而言,香港其实是最薄弱的,相较之下,台北的当代文化最活跃,北京的历史文物最丰富,但是,在国际舞台上的演出——不论是参与或者是观光客与人口的比例,香港却是最高的。台北和北京都不太懂得要如何将自己的内涵呈现出去。我们说,香港最“国际化”的意思就是,香港比较懂得用国际的语言和手段“呈现”自己。
所以国际化是一个呈现的能力。但是不要误会为那只是表面的包装和行销。就譬如学习英语,一个把英语的文法学得烂熟,语汇背得特别多的人,不见得会使用英语,因为语言的背后藏着习俗和价值;不懂得这些习俗和价值,是不可能真正掌握一个语言的。
可以正确地拼写出democracy或者civil society的人,不见得会用这两个词。或者说,会使用这两个词,指的不是只会拼写或发音这两个字而已。同样的,当我们所谓懂得国际的呈现方法,一定意味着懂得国际的内涵——文化的问题、政治的发展、市场的运作、竞争生态的改变、新思潮的涌现等等。掌握了对内涵的了解,心中有一个标准,才可能知道如何呈现可以达到目的。
有了这个标准,“闭门造车”的可能性就减低了。我们会比较知道要做什么才能和国际“接轨”。一个让人看得懂的网页、一个让人觉得亲切的机场,一个城市让人看得见它的美好、认得出它的特别,都是“轨”接得好不好的问题。可是接轨的意思,是把自己的轨道和别人的接上,以便于将自己的货物输出。轨道,与国际一致,火车里的货物,却得力求独此一家,否则,没有独特风格,谁要你的输出呢?
不是把自己淘空换别人的内容
如果我们有优秀的文学作品,那么国际化就是懂得如何将这些作品推销全球,譬如哈利波特的全球化。但不是让我们的作家模仿哈利波特的写作内容。如果我们的石库门、四合院文化是一种独特的美学,那么国际化就是懂得如何保存这个美学而且将它发扬光大,吸引全世界来欣赏它。
国际化的意思,不是把自己淘空,更不是把自己的内容换成别人的内容。道理何其简单:谁要你模仿的、次等的、没有性格没有特色的东西呢?
巴黎要跟纽约竞争,会把自己的老房子老街拆了去建和纽约一样的高楼大厦吗?那会是一个笑话。人们不辞千里去看古罗马,是为了什么?人们不辞千里来看北京城,又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来看北京的超现代高楼或者法国人设计的模仿巴黎香榭丽舍的王府井吗?
我们的建筑,已经找不到自己的词汇。我们把土地和城市提供出来,让别人实验他的词汇,驰骋他的想像。我们的音乐走西方交响乐团的路线,走不出自己的路。我们的文学,有一点国际输出,可是其中有相当的比例不是汉语的精华,而是满足他人猎奇心理的投其所好。我们的视觉艺术,要界定自己的“当代”,还有困难。
我的问题是:你要求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独立的“当代”,请问你那个土壤在哪里?当土壤非常薄的时候,创造出来的东西,当然除了性的大胆、文革的恐怖、毛的讥讽之外,就是西方的模仿,不论是建筑或是音乐。而你可能被接受,只不过因为你是“神秘”的中国,所以拙劣也可能被当做观赏的对象。我觉得我们要对自己非常苛刻地追问,要有自己“当代”的花朵出来,请问你的土壤在哪里?
实验、寻找属于自己的“当代”
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看林怀民的云门舞集。林怀民接受的是美国现代舞的训练,开始回到台湾去创建舞团时,自己就已经很清楚了自己的位置,他说:“我如果只是跟着美国现代舞这样走下去的话,到最后就只不过是一个现代舞团罢了”。于是他开始深入中国的古典和台湾的生活:京剧、楚辞、太极拳、书法、台湾本土诞生的历史、乡土信仰里的“怪力乱神”……最优雅古典的和最生猛原始的,都成为他创作的泉源。
我有一次在维也纳看云门演出。民间信仰的乩童,经过现代舞的诠释,上了舞台。“魅”的文化和“去魅”的努力交揉;林怀民在实验、在寻找他自己的“当代”。
云门舞集成为蜚声国际的亚洲舞团,和柏林的、纽约的、伦敦的各色舞团做激烈的国际竞争,头角峥嵘。云门一年12个月国际的邀约不断,两年后的档期都已满,也就是说,它娴熟国际的“呈现”手法,在国际的“轨道”上奔驰,但是它的火车里载的,可不是美国现代舞的模仿,也不是卖弄的东方情调。火车所输出去的内容有楚辞、太极拳、行草书法、红楼梦,有闽南人的悲欢离合、信仰与失落,有欧美的现代元素,综合吐纳出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当代”。
把铁轨接好,让外面的火车送货进来,同时让自己的火车开出去,盛满自己的东西。当“国际化”被误解为模仿和抄袭的时候,我们的城市就逐渐失去它自己的面貌,走到哪里都似曾相识。我们的音乐和艺术,带来的是二手的感动。
国际化是设法将铁轨铺好,找到衔接的地方,却不是把火车装进别人的货物,抛掉自己的传统。传统从来就不是死的,死的只是我们自己的眼睛。传统永远是活的,只是看你当代的人有没有新鲜的眼睛,活泼大胆的想像力,去重新发现它,认识它。
因此,在全球化排山倒海而来时,最大的挑战可能是到底我们找不找得到铁轨与铁轨衔接的地方,也就是西方跟东方,现代跟传统,旧的跟新的那个微妙的衔接点;找到那个点之后,大概就可以在全球化的大浪里,找到自己真正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了。
(来源:联合早报,作者:龙应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