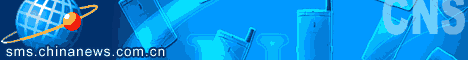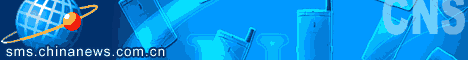(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她是中国当代文学圈里绝对的“另类”:她毫不掩饰地自恃美貌,在文字里对性爱浓墨重彩,却大肆针砭卫慧们的“集体精神贫血”;她的作品因为性和官司备受争议,她却始终被正统文化圈欣然接受。她今年42岁,她说——
“爱写作就像爱男人”
记者/粲然 丁尘馨
也许,多年以后,修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时,人们将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难题”:一个出格、离经叛道的女人的文字,在这个波澜不兴、大师缺席的新世纪小说界,令人无法归类。
虹影无疑是近年来中国最富争议的小说家。1997年,其成名作《饥饿的女儿》获得颇具权威性的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循规蹈矩的正统文化圈因此破例向她伸出接纳之手。
她一面毫不掩饰地自恃美貌,在文字里对性爱浓墨重彩,一面却大肆针砭国内以卫慧为首的所谓“美女作家”们的“集体精神贫血”,她称她们只“重视个人感情生活,对社会变革无动于衷”。
然而她的两部长篇小说均使她官司缠身、心力交瘁;同时,围绕着《英国情人》(原名《K》)是否以真实人物生活为历史背景,是否“侵犯他人名誉”,也引发文学圈对“文学与法律”界限极大的争议。
她的书起印数大都在10万本以上(这种情况在国内一流的作家中仍不多见),并常名列各大书店畅销榜。
她的身世经历也颇为传奇:私生女、出生在大饥饿年代,成长于长江边的贫民区。18岁离家出走,选择流浪和写诗。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所谓“疯狂约会,疯狂写作,疯狂做爱”的文学“黄金期”后,1991年她远赴英伦,和知名学者赵毅衡结婚。
她已42岁,评论家李敬泽说:“当年,她倾倒众生。现在依然是。”
虹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她的经历对她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写作中她的真实感受又是怎样?
12月27日下午,圣诞的欢乐还残留温度,虹影在英国的家中接受采访。谈话中,她经常停下来,放肆而妩媚地哈哈大笑。她说,阳光很好,她花园里的玫瑰仍茁壮繁茂。
“靠写性来吸引读者是低级趣味。我的小说是女性自己的性发现”
(虹影的新书《上海王》刚刚在中国上市,描写了一名妓女“成长”为旧上海十里洋场黑帮老大的故事,被舆论称作“妓院小说”。和以往作品一样,这本书一面市便因“大胆出位”再次遭遇争议,但出版社首印10万本)
新闻周刊:新作《上海王》到底写了什么,令人不能接受?
虹影:我实际上在写个人对1927年前上海的见解和感觉。当时,上海是整个中国现代性的浓缩,“妓院”只是个隐喻。
新闻周刊:这个故事大部分场景都发生在妓院里,但你却否认它是一部“妓院小说”?
虹影:它当然不是一部“妓院小说”对我来说,一个青楼女子是最下层的,那些女人的心计比《红楼梦》里还来得直接。她们靠自己的色艺幸存于上海,本是一种很尴尬的生活状态。
我喜欢这些青楼女子,我可以重新写出她们的命运。我的主人公虽然身在青楼,是被人利用摆布最惨的,但又是很要强的一个人,这一生,一步步走过来,最后才明白什么才是她真正需要的。
小说就是讲述了一个女性在现代化形成中的种种处境,这处境也包括她的性自觉的过程,和对自己的身体的发现。
(虹影的小说,从《饥饿的女儿》、《孔雀的叫喊》、《英国情人》到《上海王》,无不让主人公几乎都为女性,身处一个宏大的时代背景,她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演绎命运的跌宕和无常,这种写法在当代中国女作家中是极为少见的。她因此被称作“脂粉阵里的英雄”。而每部作品中都会有大量对主人公身体和性经历的描写,其篇幅和细致在与她同龄的作家中也是少见的)
新闻周刊:可以说,性描写一直是大众对你小说争论的焦点。这是你为吸引眼球有意为之吗?
虹影:靠写性来吸引读者,是低级趣味。我的小说是女性自己的性发现,也就是发现自我。或者说,发现自己的现代性。
传统中国女性,似乎几千年没有过性高潮。这部小说(《上海王》)中,我觉得得意的地方,就是我安排了女主人公的四段高潮幻觉、四重奏,渲染了四种色彩。
新闻周刊:你和卫慧她们那些被称作用“身体写作”的作家有何不同?
虹影:我和与所谓“身体写作”的女作家不同。她们写作,仅仅写一个房间,当作展览馆给人看。但我写,是写自己的一个连着一个环环相扣的房间。
“饥饿”是我的胎教,那是我根本无法再经历的世界
(小说《饥饿的女儿》被虹影称为“自传体小说”,这使1997年35岁的她一举成名。小说讲述上世纪60年代大饥荒时代,长江边上贫民区女孩成长的故事。虹影解释,《饥饿的女儿》既是那个时代人对食物的饥饿,也是灵魂上的饥饿,同时也是性的饥饿)
新闻周刊:从成年到1997年,为什么事隔近20年,你想重新提起这段经历?
虹影:我觉得这本书达到了一个目的,就是使我的家人更理解我,更了解我。我的母亲非常骄傲,再也不觉得生下了我就像霍桑的《红字》一样,是一个耻辱,在她的脸上印着。当年她曾经抵抗一切把我生下来,把我养大,她觉得非常值得。
(虹影母亲怀过8个孩子,死了两个,她第6,是幺女,是母亲的私生女,给母亲家人带来了无尽的困扰和麻烦,从小她就感觉自己是个多余的人)
新闻周刊:在写《饥饿的女儿》时,你说曾经想到过自杀。那段经历那么不堪回首吗?
虹影:写完这部小说,等于我重新经历过一遍地狱就是我以前的那种生活。那是我根本无法再经历的世界,但是我又重新进去了,我根本受不了。
写它的时候我肯定很平静,但是我觉得我退出来的时候更贴近从前那个世界,我整个状态不对了,所以有一年时间我需要跟英国的心理医生见面。
“饥饿”是我的胎教。以后不论遇上什么天大的苦事,我想,我不吭声,熬过今天,度过明天我就有后天。我只要活下来,我就肯定有一天会比现在过得更好。我知道在整个一生当中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我想我咬着牙就可以顶过去。
新闻周刊:你在很多文字中提到80年代的文学黄金期“人们疯狂约会,疯狂写作,疯狂做爱”,那时你最疯狂的经历是什么?
虹影:我有10年的时候在路上。(上世纪)80年代,我称之为“黄金时代“,出现了很多很优秀的人。从艺术方面来说,那段时光对我一生影响最大。
那是我的一个大学。我觉得我的经历跟高尔基特别相似,童年是我作为作家的最早的训练,然后是社会这个大学。我阅尽人间悲苦,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包括比我的家庭更惨、更不像人一样活着的人。
新闻周刊:现在你的生活条件优越而稳定,可你说,你眼中永远有一种恐惧,你在恐惧什么?
虹影:恐惧来自于外界对我的偏见。比如从我未出生开始,人们就把我看成带着耻辱的符号一个私生女。我的离经叛道从来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比如现在一些评论家把我列入“黑名单”——拒绝读“虹影”,原因是“虹影是官司作家”,等等。
“我想直到老,我都会觉得自己很美”
(虹影从不说自己是美女,她说,我是镜头里最美的女人。写小说时她喜欢面前放一面镜子,她解释并非是为了看自己,而是为了看她制造的那个想象的世界)
新闻周刊:你的小说中,女性身体的美丽都是通过性得以绽放,而且全是离经叛道的性。你认为现实就是如此的吗?
虹影:在所有女人成长的过程中,都会遇到两难的选择,不同的选择引发截然不同的结果。要做“离经叛道”的女子,需要很大的勇气。但也会有很大的收获。
我的成长过程,从来没有受到女人应得的呵护。我一生就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女人——女人应当有权享受软弱,享受手足无措,享受被人原谅“见识短”——没有这事,我从不存有这种奢侈。
新闻周刊:而你目前处在一个稳定的婚姻状态中,没有了离经叛道的经历,你觉得一个42岁的女人,将如何维持身体之美?
(回答这个问题时,虹影狡黠地避开自己关于“性塑造美”的理论。她只说有一年在北京过的圣诞大PARTY上,她打扮成一个“小女生”,为的是“避免艳遇”)
虹影:直到现在,我的身体还很美。一直都像个小女孩。体重保持在96~102斤之间,三围从来没有变过。我想直到老,我都会觉得自己很美。
我还要去那些我没走过的地方,让写作从40岁重新开始,我还保有无穷无尽的想象世界。
虹影承认自己自恋,坦言自己的小说中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影子,她说希望她本人就是备受争议的小说《英国情人》中的“林”。她甚至这样描述自己和书中主人公的“相遇”——“于是我们在某一天,就成为一本书的纸和字,无法剥离。好了,现在你可以跟随我的声音,跟着我的脚步,和我一起回到书页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