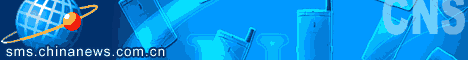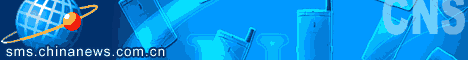最近又有一些上访者在北京制造了一些非法上访的事端,上访再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从去年1月1日到11月26日为止,共收到上访信件52852封,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五分之一;同时,来全国人大信访接待室上访总件数为17063件,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三分之一。上访问题成了我们这个社会一个特有的难题。
上访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西周就出现了“击登闻鼓”的申诉方式,汉代更是出现了“邀车驾”即在皇帝出宫或出游时拦车鸣冤的申诉方式,这些申诉方式大都延续至封建清王朝,并深深在国民的性格中扎根。解放之后,由于人治成分过高、公权力配置失范和政治运动等原因,上访一直绵延不绝。而在市场经济全面实行的今天,由于市场机制本身的不健全,各种利益的分化,社会不稳定因素的积累和扩散,局部地区社会矛盾的激化,上访的浪潮此起彼涌。
在对待上访问题上,各级党政部门一方面确实是从为民服务的思想出发,党委、政府、人大、法院、检察院一齐上,对上访所涉问题高度重视,千方百计为群众分忧解难;另一方面,又对缠访、滥访扰乱国家机关正常工作秩序乃至于社会秩序不胜其烦,于是便有不少地方对上访者围追堵截。而上访群众从领导的重视看到了希望,从围堵感到申诉权被侵犯,更加坚定上访决心,上访问题陷入了循环的怪圈。
从根本上讲,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紧紧抓住发展这一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推进社会民主与法治的建设,是解决上访问题的根本性出路。但如果我们从制度建设上去分析,我们会发现,社会矛盾纠纷在任何社会都客观存在,这就不能不让我们去思考纾缓社会矛盾的有效机制。在西方国家,司法是纾缓社会矛盾纠纷的通道,是避免社会因矛盾纠纷而崩溃的人为屏障,司法从来都是以定纷止争为天职。然而我们遗憾地看到,我们的司法机关在这场上访浪潮中扮演的是日益边缘化的角色:一方面许多矛盾纠纷的解决根本无法进入司法途径,另一方面司法机关的最终裁判屡屡在外部权力迫使下而被推翻。前者使得纠纷不能在正当程序中得以充分而理性地张扬与解决,而后者又使纠纷永无宁日,简而言之,司法终极性的缺位是我国上访不断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司法终极性的第一个含义体现在法院或其他具有司法性质的机构应是大多数社会矛盾纠纷的最终裁决者。社会的大多数矛盾纠纷最终要在法定的程序内,由中立的第三方在双方平等的参与下加以公正地解决。司法解决之所以优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在于其有法定程序的保障,裁决者的中立、纠纷双方地位的平等,并提供了充分的说理场所,充分保证了矛盾和冲突在体制内的解决,并且形式上保证了承担败诉的后果是说理不充分者,正当程序有利于消弭愤怒与不满。而要做到上述要求,司法独立是关键,其一法院与法官要独立,法官无上司;其二是司法机关对所有司法性质的问题享有管辖权,并应有权威裁决提交其的问题是否属其管辖范围。
司法终极性的另一个含义是裁决应有既判力,已作出的裁判不允许随意改变。当前我国终审司法裁判的重审有五个“无限”,即提起主体无限、时间无限、次数无限、审级无限、理由无限,如此无限在当今世界绝无仅有,而这也正是当事人上访、缠诉的重要根源之一。在保证纠正明显错误裁判的前提下,实行有限再审,提高诉讼效率,维护裁判权威,应是审判制度改革的大势所趋。与此同时,各级党政领导不应再充当救世主的角色,不能也不要再越权作出各种批示。其他国家机关权力配置应规范,包打天下的局面应改变。经过司法程序裁决的社会矛盾纠纷的申诉,改造为当事人的一种再审诉权,由司法机关在法定程序依有限再审原则加以解决。
当社会的大多数矛盾纠纷最终解决纳入了司法程序并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司法的公正,当司法裁判的既判力得到应有的尊重,当司法终极性这么一个西方理念深入国民的骨髓并成为他们法律意识的一部分,在不久的将来,上访现象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少。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和看到,这种司法终极性的实现需要一定的前提和基础,比如首先就应该尽量确保司法本身的公正。而这种司法公正又是与司法独立、法官本身素质的提高等紧密相关的。而这些又需要在现实当中减少和消除各种对法院干预的行政权力,需要健全和完善各种监督机制和制度。否则,如果司法本身不公正,司法的终极性也就失去了合法性基础,也就必然难以让人民认同和服从,各种上访和不满自然也就难以杜绝了。(法制日报/杨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