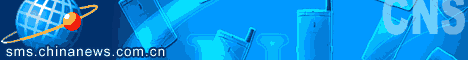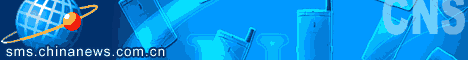文/南妮
一个孤独的女子改写了“好死不如赖活”的传统生死观
2003年12月30日早上,一个没有阳光的阴郁冬日,坐出租去上班。
“梅艳芳死了,你知道吗?今天凌晨的事。”刚刚在车中坐定,司机劈头就来了这样一句。
这一个惊人的消息扰乱了上班的节奏。脑子里像电影闪回镜头一般,速速掠过一串画面与数字。从2003年9月5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证实癌症距今才3个多月,从11月6日在红体育馆带病举行8场演唱会一直到死才1个多月。生命最后的行程被梅艳芳控制着,连死仿佛也有着预计。这般刚烈的、决绝的死属于梅艳芳,除此外,你想不出还有什么方式更配她的。
12月的《时尚》杂志,刚刚读完才没多久,这篇写梅艳芳的叫做《一个人的嘉年华》看得人唏嘘。“义气,这个很少用在女人身上的词,却是她的标签。”“爱小男人,却又无法享受心安理得控制男人的乐趣,哪怕再容让,也是令人压迫的豪迈,一个让字,还是居高临下。”触目的句子,联翩的浮想。义气,用在了异性身上,也用在了同性的身上,是否就是超越了女性的狭隘,但同时也意味了一份对于自己女性味的不自信。“因为我丑,所以要怪。”梅艳芳如此解释自己的百变形象。一直到11月初的舞台,那最后的告别,她穿上了珍藏的婚纱,她是明白自己不会再嫁了。为何要这般的透明?一张底牌都不剩?你真弄不懂骄傲与自卑是如何地铸造出了一个人的磊落风格。
有多少本能的东西,自卑、恐惧、或者忧虑,一直被她压制着,艺术借给了她魔术的手段,使一个女人的精神生命无限强大,强大到可以蔑视死亡。所以,她不是普通人,不是一个平凡的人。她与平庸有一个对照。
爱她的人看她那穿着华贵的迪奥衣装展示着最后的华彩,是一番什么心情?是应该去鼓掌喝彩,还是留下来悄悄地黯然神伤?激情与死亡的角逐,辉煌得悲壮而惨烈,然后死亡随之而来。5年的能量压缩为50天,上苍总是精于计算。
不再苟延残喘,不再麻烦别人,就这般率性而坚硬。真的就是,一个人的嘉年华。
梅艳芳,一个孤独的女子改写了“好死不如赖活”的传统生死观。她的凌厉与勇气也使得我们少却了一点“闻死丧胆”。在享受的都市,存在本身就意味着一份希望。有多少人愿意保有细水长流的殷实,就有多少人采取“宁弯不折”的中庸。瞬间即是永恒的话已经被说烂,但瞬间毕竟只是瞬间。
晚上,在2003年的最后一天,无意间放了一张许美静的CD。听不懂的粤语却听得泪流满面。在麻木与日常间僵硬的心灵很容易会被一丝飘逸的声音击中,就像一次向死亡挑战的伟大表演使你重新思考关于生与死的问题。一个只活了40岁的艺人。也许,她只向我们——观众,演示了一半而自己又藏了一半。她向我们展示的是称得上完美的一切包括完美的努力。这就是一个艺人的一生啊。娱乐众生是她追求的舞台聚光。
为何豪迈是令人压迫的?为何居高临下仍令人怀揣怜悯?是不是这一个大女人的内心从没有做小女人的自信?——那样一种随心所欲依赖一个男人、吃定一个男人的慵懒散淡?永远是干脆与坦荡,连心计也没有。是不屑,也是不自信,连尝试都一并放弃。只握有自己能够控制的。每一步都辛苦地去做,最后就拼死了自己。
艺人,他以自己的心火血性改变着我们生活的平庸面貌。他体现着时代的繁华丰盛歌舞升平。他是我们不息的夜莺。除了才华,艺人,应该是有着人格魅力的。梅艳芳,结束了一个时代。不大会再有这样自律的艺人。
并没有想到,2003年结束的那一天,是怀着如此的哀痛与理解去追思一个特殊的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