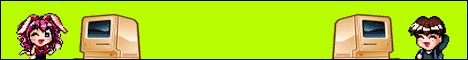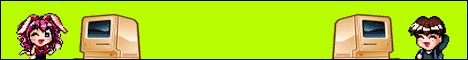日前,张艺谋正在北京秘密拍摄新片《十面埋伏》,作为继《英雄》之后的第二部“张氏武侠片”,媒体和观众都对这部讲述两个捕快和一个盲歌伎的爱恨情仇的影片议论纷纷,猜测《十面埋伏》的故事是不是还像《英雄》那么单调。同时,《广州日报》又登出《张艺谋“堕落了”》一文,把张艺谋的老师周传基和作家石康对张艺谋的批评放在了一起。文中提到,周传基认为张艺谋的影片中《大红灯笼高高挂》是最好的,再以后的就不好了,而他的商业片没有想像中好;石康则说张艺谋“和暴发户没什么区别”。一时间,张艺谋又被推到文化界和娱乐界评论的风口浪尖上。
难以成败论《英雄》
虽然张艺谋再三声明,《十面埋伏》不是《英雄Ⅱ》,但是媒体的评论还依然把它们放在一块儿说。针对《英雄》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方面,首先是关于主题。2003年7月底,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英雄》把秦始皇拍得和历史上的形象截然相反,是一部荒唐的电影。2003年8月,《南方周末》刊登了对两位著名文艺评论家的访谈,指出《英雄》的主题违背了历史真实和最起码的现代意识。其次,《英雄》中出现了一些跳跃和省略,相当一些观众表示“没有看懂”。北京电影学院的郝建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它很多的情节、转折、台词都不按照人之常情来”,“不符合我们普通人的思维和说话的方式”。特别是影片结尾,无名和秦王在大殿上决斗,无名的刀已经划到秦王的脖子上,却忽然“顿悟”到秦王是胸怀天下的英雄;秦王知道无名是来杀自己的,却把剑扔给他,并且在最后认识到“剑”字的真谛在于和平,这一系列转变都显得有些随意。郝建认为,《英雄》是张艺谋转向主旋律文艺的顶峰,艺术上可能依然很漂亮,很有力,但却是一种“思想上的迷失”。
媒体的批评相比之下则更为尖刻。曾有记者嘲笑张艺谋“花了几千万美金却以‘打架’吹出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彩色肥皂泡”,非常失败。但是,记者采访的几位电影界教授却提出,《英雄》的票房成功有复杂的社会原因,除了商业炒作外,与张艺谋的社会影响力以及不同受众的审美取向都有很大关系,不管《英雄》好看不好看,张艺谋能造成如此大的社会影响,也可以说是一种成功了。
艺术、政治、商业,“一个都不能少”?
其实,张艺谋从《红高粱》到现在的《英雄》,电影风格数变,关于其电影的争议也一直没有平息过。1987年,张艺谋出演影片《老井》,获第二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同年执导的影片《红高粱》获第三十八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之后,他投身商业电影中,连拍了《古今大战秦俑情》和《代号“美洲豹”》,由于当时的商业片并不能给拍片人带来多大的好处,他回到老路上,在1990年后拍摄了《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等几部影片,继续在戛纳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等国际电影节上捞到不少奖项。1995年后,商业片骤然吃香,于是《有话好好说》顶着“谁说我不会拍商业片”的旗号热映一番。但是,国人对他的电影并没有像国际大奖的评委们那样一边倒地认同。一部分国人称赞张艺谋为国争光,但也有不少人,尤其是一些海外华人,认为其早期电影以描写中国的落后和丑陋来迎合西方的阴暗猎奇心理,让每一个在海外或者到海外的中国人承受了鄙夷和羞辱。
也许正是迫于这些说法的压力,张艺谋后来的作品其实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的。郝建指出,《一个都不能少》是张艺谋电影的一个转向,从认同个体、写个体的需求转向写崇高和光明的主题。张艺谋曾在1999年致函戛纳电影节主席,以该主席称《一个都不能少》明显是在替政府宣传为由宣布退出戛纳电影节。郝建认为,张艺谋写这封信,是“在多年忍受了‘表现丑陋和落后’的骂名之后,终于有了面对国际大奖扭头就走、大声说‘不’的机会”。郝建认为,《一个都不能少》是张艺谋在《活着》没有通过电影审查之后,“适应主旋律文艺观和电影检查体制的一个转变”。但是,正是这种转变,使得张艺谋背上了“投机”的骂名。有人认为他为了通过电影检查不惜牺牲电影的艺术性,但又不肯承认。《深圳文化采风报》曾登出一篇文章,认为“张艺谋从这部影片中透露出来的患得患失心态令人担忧。政治上要讨好,商业市场要讨好,艺术上的追求还不能舍弃了”。
还有人认为,张艺谋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一直对商业市场察言观色,拍《英雄》更是“由面对内心的艺术家转变为面对票房的电影商人”。然而,接受记者采访的几位影视界教授却表示,张艺谋十几年来的发展是可以理解的,他不过是适应了社会的发展,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而对于一个电影人来说,这种适应并不可耻。
如何为中国电影谋
无论人们怎样争论,不可否认的是,张艺谋是中国电影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有人说,很难想像近20年来的中国电影,如果没有张艺谋会是什么样子。著名评论家余杰在今年8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虽然《英雄》很有问题,但是张艺谋前期参与的一些影片,像《老井》,应该说很有成就,很有创新,给中国沉闷的影坛带来了冲击。张艺谋1984年拍摄的影片《黄土地》,充分调动摄影手段,以独特的造型表现出黄土高原的拙朴浑厚。他1987年导演的影片《红高粱》,以浓烈的色彩,豪放的风格,融叙事、写实与写意为一体,发挥了电影语言的独特魅力。《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有很多艺术上的创新,周传基欣赏这部影片也可能是因为这一点。但是,《英雄》中却没有任何艺术创新的成分。郝建认为,就艺术影响来说,《罗生门》影响了无名与长空决斗那一场;绸子底下做爱和在大殿中挂满绸子是受《末代皇帝》的启发;锣鼓点子和打击乐器的使用是从胡金铨那里来的。用别人的元素无可厚非,但遗憾的是《英雄》里面没有超越和创新。所以有人认为,《英雄》是张艺谋“艺术的堕落”。
从这些争论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出,电影学术界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对张艺谋的态度比较宽容,而媒体代表了一部分普通民众的感觉,对理论不感兴趣,因而显得更为苛刻。其实赞同也好,批评也罢,大家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让中国的电影更好看,对于这一点,想必张导演也同意吧。
来源:环球时报 作者:赵颖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