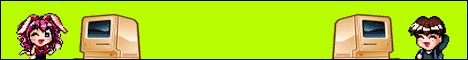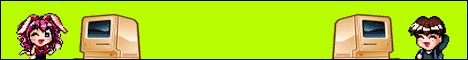不愿放下手中的笔
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巴金几乎每年春末夏初,都要到杭州西子湖畔去疗养一个时期,直到1999年春节前后,因疾病加重,无法离开上海华东医院,从此再也不曾去过杭州。
在杭州虽说疗养,实际也和在上海家中一样,每天赶着把八十年代后期就抓紧做的《巴金全集》编读工作,一卷又一卷地审校,还每读完一卷,就写成一篇“代跋”;并由此通过与责任编辑王仰晨(树基)通信形式,叙述当年写这些作品时的心情,抒发对每一卷内容有关的人事怀念,既可以看出作者今天对这些作品的评价,更有助于读者对这些文章背景的了解。
但也正是由于在完成《随想录》一百五十多篇写作后,巴金仍不曾放下他那坚强的笔杆,他在九十岁(1994)以后身体确实越来越显得衰老了,不仅头发全白,他那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更加严重,“文革”结束后不久就患上的帕金森氏病更使他行动受到影响,连笔也愈来愈不听使唤;同时由于身体严重缺钙,引起胸脊椎骨折和体位性血压波动。他在八十年代中期还可以站在特制的圈车里走动,而现在只好坐在轮椅上过日子;当然,每天几乎有一半时间还是躺在床上。
生活状态尽管如此,他还是在轮椅上架起一块木板,当作书桌,颤颤巍巍地写出一篇篇短文。这些短文中,特别令人难忘的是《最后的话》、《没有神》和《讲真话》三篇。《最后的话》是《巴金全集》第26卷,即最后一卷的一篇“代跋”,它先发表在巴金主编的《收获》双月刊上。在它发表后,巴金又写了《讲真话》一文,说他写《最后的话》是“希望读者理解我。我这一生是靠读者养活的。《全集》出了二十六卷,但是要我自己看,至多只有一半可以流传。……我现在虽然走在生命的尽头,但是……我是主张人要有理想,要面向未来,人不仅要顾自己,还要顾子孙。……”
《没有神》文字更简短,就这么几句话,但反映出巴金内心对过去的痛苦,与对未来的真诚与坚决:
“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还会再做梦吗?为什么不会呢?我的心还在发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梦了。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谁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进入梦乡。当然我也不再相信梦话。
“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近一千万字的《巴金全集》在1994年春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全部出版。
在《巴金全集》出版后,人们以为巴金过了九十岁生日,对自己的写作生活总该告一段落吧,出人意料他与他的责编王仰晨又掮起了另一个重大任务:编辑出版《巴金译文全集》。把自己几百万字的译文重新整理出版,原是巴金的一个心愿,经王仰晨提出,他当然答应,但却拖延了一些日子。恰好那天老友黄源来访,两人谈起当年在鲁迅、茅盾身边,共同投身于《文学》和《译文》这两本杂志的编辑工作的情景,禁不住引出许多话题来。当黄源知道巴金怕过去译法有误而在出版《巴金译文全集》时无法一一改正时,便说:“你的翻译作品,也是你一生工作的重要部分,让人民文学出版社帮你整理出版,是件好事,你来不及一一校读,每一卷写一篇代跋,交代一下当年工作背景,就足有史料意义了。你目前无法重读,也就让它保持原来面目吧。”巴金这才又鼓起干劲。三年以后,1997年10月,巴金把刚出版不久的《巴金译文全集》精装本十卷,在杭州西子湖畔赠给前来送行的黄源。黄源这时也有九十多岁了,兴奋得两眼露出晶莹的泪珠,翻开第一卷第一页,见到了巴金请他侄女李国#代为题签的几个字:“河清兄,第一次样书。”下边是巴金在上午就亲自把着自己颤抖的手写的“巴金”二字。黄源说:“上次《巴金全集》是你的一半,现在《译文全集》也出版了,那是你的另一半。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巴金了!”
说实在的,那时帕金森氏病已使巴金很难自己握笔,写成一篇完整的文章了。《巴金译文全集》中的代跋,不少篇章是靠巴金口述,由李小林记录,然后由巴金修改定稿的。有时小林来不及记录,则由侄女国代理。但这些代跋,仍完全是出自巴金内心的。十卷译文集,就有十篇“代跋”。它们和《巴金全集》中二十多篇“代跋”一样,反映了当年巴金译成这些作品过程中的心境和情景。比如第一卷代跋,叙述怎样把克鲁泡特金《我的自传》翻译成中文时,巴金就禁不住想起六十多年前老友吴克刚对他的帮助;同时也很自然地引起他对另一个朋友汝龙的怀念。在写第二卷代跋时,巴金难忘的是当时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与丽尼、陆蠡两位友人怎样分工,完成《屠格涅夫选集》的翻译工作。在第三卷代跋中,想到的是《处女地》在印成后带回到上海时情景,当时抗战刚胜利,而友人陆蠡却已遭日寇杀害。到六十年代初期,曾下决心改译《处女地》,却因忙乱没有完成,直到“文革”期间受尽迫害,最后下了“敌我矛盾作人民矛盾处理,不戴帽子,作翻译工作”的结论,而家里书房仍给封闭着,只好坐在汽车间楼上的小房间里重译这部“四旧”。到了1978年,《处女地》才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而这时老友丽尼也已去世多年了。
除了八十年代完成的《随想录》这部划时代的著作,和九十年代以巨大精力编定的《巴金全集》和《巴金译文全集》外,他在九十年代出版的书,还有《巴金书信集》、《巴金七十年文选》、《家书》、《没有神》、《再思录》、《巴金美文精萃》、《十年一梦》、《巴金谈人生》等。这些书从各种不同视角,展示了巴金各个时期的感情和思想。在1995年为《再思录》写的序中,他曾说:“躺在病床上,无法拿笔,讲话无声,似乎前途渺茫。听着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乐,想起他的话,他说过:‘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欢乐,你就到人民中去吧,你会相信在苦难的生活中仍然存在着欢乐。’他讲得多好啊!我想到我的读者,这个时候,我要对他们说的,也就是这几句话。我再说一次,这并不是最后的话。我相信,我还有机会拿起笔。”
应该说,巴金在新世纪来临的前夕,尽管病残体衰,捏笔困难,不论坐在轮椅上,还是躺在床上,始终不曾想到过要把笔放下。
迎来了新世纪
坐在轮椅上的巴金不曾忘记社会上发生的每一件大事。1999年以前,不论在上海,在杭州,在家中,在医院,他每天傍晚总是收听收看电视广播节目。除了把所有重版书稿费一律汇向中国现代文学馆外,他还把新写文章的稿费也积聚起来,不时捐献给发生洪、涝或地震的灾区人民。他一看到灾区受困,就请上海作协陆正伟送去一份并不留自己名字的捐款,连1998年四月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他获“杰出贡献奖”得到的一笔巨款,也用“一个老人”的名义捐给了灾区。同时他还十分关心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他几乎每年都给“希望工程”办公室捐款几千元或几万元。
他继续向有关单位捐赠藏书。1997年5月6日下午,他还破例走出家门,到上海图书馆观看即将举行开幕礼的新馆。他过去已给上图捐赠过7000册外文书籍,这次又请侄外孙李舒在家里为他整理出4000多本珍藏的外文图书,这些书几乎每本扉页都有巴金的英文签名,其中有俄文版果戈理《死灵魂》、法文版卢梭《忏悔录》,还有一套十卷本的俄文版《托尔斯泰选集》,都是巴金平时爱不释手的宝贝。据《与文化名人同行》作者、在上图工作多年的肖斌如说,那天巴金由小林、小棠陪伴着坐汽车来到淮海中路上海图书馆知识广场,停车后,从车内出来,坐上轮椅。馆长马远良上前向老人家献花,表示欢迎。巴金说:“我是一个中国作家,应该为我们国家的图书馆作点贡献。”小林、小棠把轮椅推到目录大厅,吴建中副馆长就在一台电脑上操作。巴金看到自己所有著作都在银屏上显示出来,禁不住笑了。轮椅从一楼推向三楼,让巴金看到了图书馆每个房间里读者找书、查书、读书的场面;最后来到“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巴金看到许多他所熟悉的作家手稿,和他自己过去写下来的一些字迹,由此引起了对往事的怀念……这次出行,也许可以说是巴金最后一次对外单位的访问。
1998年,巴金发表了他的最后一篇抒情散文《怀念曹禺》。这是继《怀念萧珊》之后,巴金晚年散文中的又一株枝叶共茂的大树。巴金坐在轮椅上,对小林苦笑着说:“我还想写一篇回忆西谛(郑振铎)的……”但是就在这一个时刻,1999年春节前几天,巴金的健康进一步恶化,突然发高烧,患上肺炎,头脑昏昏沉沉。华东医院医师立刻把他转到重症监护病室进行抢救,因痰塞呼吸道,不得不把气管切开——从此,巴金再也无法说话了!在手术治疗过程中,因防细菌感染,医院严格规定,除了家属和护理人员,谢绝一切客人前去访问,连平时至少每周都要去探访一次的胞弟李济生,也是直到三个月后,险情过去病人重返正式病房,才准许他前去看望。
巴金见到济生,仍禁不住露出一层笑意,但无法更明确表达他的内心激动。济生忙说:“你吃力不用讲话,还是听我说吧!”他就把这一时期几位老友经常打电话问他病情的情况告诉他;同时还把外地及海外友人来信摘要念给他听。济生深知四哥最重友情,他的朋友最多,虽在重病中,仍十分想念他们。去年春夏巴金去杭州休养,临行还关照济生去问候正住在华东医院治病的柯灵与罗洛,而今罗洛已不幸逝世;柯灵虽已暂时出院,哪知另一个老友王西彦也住进了华东医院。济生记得西彦曾几次向他表达对巴金的关心,他们是在“文革”中患难与共长达十年的难友啊!当然,此时济生不可能预料到西彦、柯灵不久即先后离世,他只能转达两人对巴金的问候之意。说着话,见巴金又昏沉沉想睡了,便离开了病房。
隔了两天,济生又去病房看四哥,恰好小林正守候在巴金病榻边。他想起了前些日子读到的张光年在《沪苏日记》一文中说的几句话:“回想四月初巴老心情不好,拒绝吃药……”就忙问小林是怎么一回事。小林说:“爸爸在险境过去,病情稍趋稳定后,从昏睡中醒来,看到自己眼前处境,觉得自己没用,一切全听别人摆布,有违自己心愿,确实曾感到十分烦躁不安……”他明白了,四哥似乎又经历了一次艰难的自我挣扎,终于又恢复过来了。
现在,巴金已不能像过去那样按时看电视节目了,但小林她们仍让他听录音,为他放音乐。小林还特地打电话给音乐知音、家中藏有大量录音带的作家赵丽宏,请他帮忙。小赵很快给巴老送去二十盘录音带,其中有贝多芬、肖邦、李斯特、舒伯特、拉赫玛尼诺夫等人的作品。
巴金终于和千万读者一起迎来了21世纪。在1999年新年,巴金和冰心、萧乾等相约共迎新千年到来,但冰心、萧乾两位老人临时撒手归去。这件事巴金并不知道,谁也不想告诉他,怕影响他的健康。他在动手术前,曾想请家属用手机与冰心通话,家属只好推说医院与外地通电话有困难。这件事就这样打发过去了。
而今,巴金百岁大寿来到了。老人百年耕耘,果树遍地,在我们享受他的丰盛收获而感到无限欢愉时刻,我们自己该怎样挺起腰来奋发图强呢?
(来源:上海《文汇报》,原摘自《巴金传》2003年12月重版本,徐开垒著,上海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