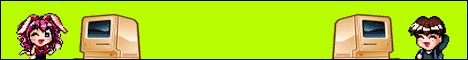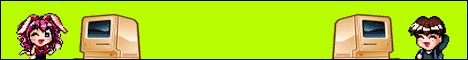一个老人的百岁寿辰到了,媒体上为老人贺寿活动的消息多了起来。老人已经不能说话,但他肯定知道又要发生什么,让女儿转达他的话:“不要拿国家的钱为我祝寿。”他自己就是一个毕生不拿国家俸禄的人。他是巴金。
多年来,巴金病重,一直住在医院,他是沉默的。若干年来,如果不是到了寿辰,如果不是有大人物去看望他,便不再有关于他的新闻。巴金属于公众人物,但早已不是新闻人物。即便如此,在互联网的搜索引擎里键入“巴金”二字,涉及他的网页仍有10万页之多。他仍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今天。
阅读巴金小说《家》、《春》、《秋》的时候,我的阅历不够,尚不能体会那个时代里的创作所表达的一切。那时的巴金,离我很远。我真正感觉到他离我很近,是他写作《随想录》的时候。
我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买到这5本薄薄的小册子后,几乎一口气读完。70年代末,当受过“文革”冲击的人们都在指责他人、社会给自己造成的种种厄运时,这位老人却开始解剖自己,开始忏悔,开始给自己的良心一个交代。以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他完全可以不这么做。人们会将他违心做的错事、说过的错话,统统推给那个时代。但是,他还是这样做了,没有任何外力的驱使。这是使我真正感到震撼的地方。
现在的年轻人读这些文字,可能觉得平淡无奇,有的知名评论家甚至讥讽那是“小学二三年级的水平”,不就是“说真话”吗?他们不知道,在巴金开始发表这些文字的时候,有人不喜欢。他们位高权重,于是即便是在香港的报纸上,不少文章也多有删节,甚至被“开天窗”;即便我们看到的正式出版的《随想录》,也是删节本。
《随想录》的精髓,说到底,确实就是3个字:“说真话”——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对历史。这是容易做到的吗?太难了!检索一下共和国的历史,哪一次灾难不是以假话开始,被假话推波助澜的呢!从国家领导人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因说出真话而遭灭顶之灾的,又何止千百。人们“聪明”了,精于算计了,算出假话可以给自己带来的种种好处,于是假话绵绵不绝。又岂止是假话,假统计数字、假账、假货、假典型、假证件、假学术……作假,早已是当代中国的痼疾之一。
巴金有不少荣誉头衔,却惟独没有权力,他不可能在制度上为根绝作假做什么。他明白,对一个以笔为生的人来说,惟一能做的就是说真话。“是大多数人的痛苦和我自己的痛苦使我拿起笔不停地写下去……我写作是为了战斗,为了揭露,为了控诉……”
如今,在公共场合,很多人只说“正确”的话。而这些“正确”的话,对不少发表言论的人来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巴金给“讲真话”列了标准:“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看起来这是个很“基本”的要求,但有多少人做到了呢?
当巴金写完《随想录》时,他已经知道此生的创作已经完结了,他说:“五集《随想录》是我一生的总结,一生的收支总账。”这时,他的手已经不听使唤,很多字是用自己的左手拉着右手的衣袖写出来的!还有最后的一件事,就是编出自己的创作《全集》。检验一个人心灵的时刻又来了。
阅读旧作,巴金感叹,从1949年到1966年,“我在17年中,没有写出一篇让自己满意的作品”。他的生命历程中曾经有过一段曲折,这就是他为了迎合当时那个时代而不得不编造一些大话空话假话,甚至有一些在政治运动中违心发表的批判性言论。对于这类文章,有些文化名人或家属是绝不同意编入自己的《全集》的。他们不希望后人知道这些“污点”,他们喜欢自己的历史是“清白”的。
巴金一定也感受到这种历史造成的悖谬的痛苦,但他的选择是,把这些文字编入全集,为的是永远让后代看清一个人在历史中的悲剧。他在一篇跋里悲哀地说,“现在才明白编印全集是对我自己的一种惩罚”。这种痛苦不是常人能够体会的,然而巴金对历史讲真话的勇气,超越了个人的痛苦。这种绝不宽恕自己的道德情操,是老人留给世人最后的遗产。
巴金长寿,但他对生死看得很淡,“想到死亡,我并不害怕,我只是满怀着留恋的感情”。当他不能再工作时,他认为活着是没有意义的,他多次向家人要求“安乐死”,这个要求当然不会被满足;他要求建立“‘文革’博物馆”,让后代永远记住中国发生过什么、为什么发生,没有人理会;他要求不再担任中国作协主席,人们也不答应;他要求不要为他祝寿,但看来声势浩大的祝寿活动已经在各地铺开……老人在病榻上无奈地感叹:“我是在为别人活着……”
有识者说,多年来,“人们在仪式上保持了对老人的尊重,但他的警告却被视为一种杞人之忧”———在巴金百年寿辰之际,这真是一句令人深思的真话!
(来源:《中国青年报》、作者:端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