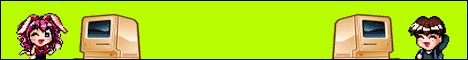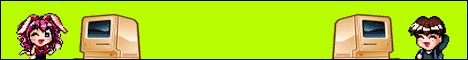编者按:今天是11月25日,适逢巴金先生百岁华诞之盛事,我们邀请与巴金老人有过较多来往的四位作家、评论家撰文,以此表达深深的敬意。
顶级寿桃赠巴金
2003年11月25日是中国文坛美丽的一天,老天爷顺从人愿,把人间一个顶级的寿桃赠送给了我们的巴金。
此刻,巴老在上海武康路的寓所一准溢满了鲜花的芬芳与色彩。华东医院那间静静的休养室想必被精心装点得生意盈盈吧。巴老脸上也一定会浮出笑意。这来自生命深处的笑意,陡然驱走了深藏在他满脸皱纹中岁月重重的阴影……想到这里,我一下子感受到一个世纪辽阔而多事的空间。一个人的生命竟有这样浩瀚的包容,而这个生命的本身又是这样的清晰、透彻而完美。
在历史的大地千千万万杂沓的足迹里,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辨认出他一个个精神的足印。他最初那些振聋发聩的反封建的文学;他后来向国人介绍西方文化经典所做的那么重要的翻译与出版工作;当然,他也有过彷徨与踌躇,但在《随想录》里全都自我校正了。这种个人的“忏悔”不是带来一个时代的心灵反省吗?跟着,他要用博物馆的方式终结“文革”,就像把魔鬼装进瓶子,塞上塞子;把严冬关在昨日,锁紧了锁———这都是在呼唤春天和安宁永驻人间。
作家总是在全身心地着意于世界时,无意中创造了自己。于是,巴金给我们一个完整的人格和水晶般透明的心灵;他从不囿于一己的悲欢,而把大地的苦乐看得至高无上;他对善恶之间的界限毫不含糊;勇敢地面对生活,也勇敢地面对自己。他用了整整一个世纪,才完成了这样一个品格。这才是巴金真正的财富,也是文学的财富。他叫我们懂得真正的文学财富,不只是一两本好书,更不是几本畅销书,而是在波涛汹涌的文字中那个透彻的人格与心灵。正如他所说的一句再普通不过的话:“把心交给读者”。但我们谁能像他这样彻底的真实与高贵?
由于老寿星的健在,许多在别处已经成为历史的,在他这里依然是脉搏跳动着的生命的一部分。过往的风景没有褪色,往日的精神鲜活如初。精神是不会过时的,也是不灭的。而百岁的巴金把五四时代进步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与人格传统一直活生生地带到今天!
我们希望这个传统传衍不断。我们祝他长寿更长寿,一是为了他本人的幸福,一是因为他是这种传统与精神的象征。
走过一个世纪
还是在中国历史新时期的开端,我与巴老有过几次心灵交融,虽然那都是偶然的瞬间,但给我留下的深邃而难忘的记忆,并没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漠,时至今日仍然鲜活如初。1983年初,巴老让我的儿子从众由上海给我带来了他的赠书《真话集》。当时,巴老因折断腿骨,在华东医院卧床。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从众,去上海为老人完成了面部肖像的雕塑,因而有缘在华东医院与半卧于病榻的巴老,相处了宝贵的几天。头部雕像完成得十分顺利,上海油雕室的同行,将其泥模翻制成了铜雕(即今天中国现代文学馆巴老展厅内那尊黑色的头像铜雕);巴老出于对隔代人的关爱,在我儿子告别上海前,特意把他刚刚出版的一至四卷《随想录》题赠给了从众———老人叮咛他,其中第三卷是题赠送我的———那就是我一直置身案头并熟读的《真话集》。其用意我全然明白:让我在作品和行为中,都要以说真话为标尺。
其实,早在1982年的秋天,我已然聆听过巴老讲真话的教诲了。当时,他从在法国举办的国际笔会归来,于北京短暂停留。我到他和女儿小林下榻的燕京饭店去看望他。记得,巴老因长途飞行,那天的精神显得十分疲惫,但他还是靠在沙发上表达了如下的心语:“我们这一代人都老了,读过你们这一代倾吐真情的文字,我常常为之感慨。你平反回来以后迈出的步子不错,一定要坚持下去。”我说了些什么,因年代久远已然无从记忆,但巴老这几句十分平常而又深邃的话,我是时刻反复咀嚼的。因而直到今天,那平缓而又安详的音容,仍鲜亮地印在我的心扉之中。说起来也是一个机缘,那时正值我描写劳改生活的悲情中篇小说《远去的白帆》遭受到封杀。那天,我将这部中篇小说的遭遇,讲给巴老和小林听了,并将文稿交给了巴老和小林。事后小林告诉我,巴老不顾长途飞行的疲劳,连夜审读了我的小说,并对小林说下如是的话:“小说展示了历史的严酷,在严格的主题中,展示了生活最底层的人性之美,不管别的刊物什么态度,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品,回去我们发表它。”因而,这部遭到封杀的中篇小说,不久就在《收获》上面世了———事实证明了巴老预言的准确,在1984年全国第二届小说评奖中,一度成为死胎的《远去的白帆》,以接近全票的票数,获得了该届优秀中篇小说文学奖。
当时巴老已年过七旬,不顾疲劳地读上几万字的长卷,并不顾可能惹来的麻烦,将描写知识分子沉沦与苦难生活的作品披露于世,这本身就是对文学表现生活真实的张扬。其实,巴老从1978年写《真话集》开始,不仅写下讲真话的承诺,并以身力行为写真实的作品鸣锣开道。
1984年底,中国第四届作家代表大会闭幕之后,新一届作协领导班子与文坛元老在北京新侨饭店欢聚。在这次聚会的间隙,我向巴老表示了一个后来人的诚挚敬意。巴老坦诚地对我说:“这要感谢‘文革’,如果没有‘文革’的十年浩劫,我也许不会急于动手写《真话集》;对待文稿,怕也难于走出过去的思维定式。”
说实在话,当我与巴老心灵对话时,心中常常不是喜悦,而是难以言喻的感伤,之所以产生如此的心绪,是源于巴老一生的创作年表。这位穿越了现、当代历史经纬的文学泰斗,解放前尚年轻时就写出《家》、《春》、《秋》、《灭亡》、《寒夜》等长卷的大作家,曾以他那枝多情的笔,影响了当时的多少青年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巴老以他的锐利笔锋,挑开了旧中国的封建家族的大幕,呼唤着新时代的一轮骄阳。可是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文革”结束,在这长达二十多年的光景中,除了50年代初期,巴老随军入朝后留下了小说《团圆》外(后被改成电影《英雄儿女》),一直到“文革”结束的1976年,老人留下了漫长时间内的文学空白。这种文学上的空白,里边藏满了难以言喻的沧桑,如果以巴老年轻时的文学成果,来对比巴老的后二十年,不禁让人产生田园荒芜的感慨———但,这不是巴老个人的悲哀,这种空白几乎覆盖了中国文坛的一代元老(包括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一生安然自处与世无争的巴老,也不能逃脱时代赐予他的文学伤痛。因为那年代的时间总合,约占巴老生命年轻的四分之一,加起来有几千个日日夜夜之多。因而,当老人到了生命晚年,面对夕阳静思其苦乐人生时,情不自禁地呼吁文人的真话,而不是违背心意的连篇假话。
当笔者写此祝贺巴老百岁生日文章之际,小林正好打来电话。我询问巴老的身体状况,并请小林转致对巴老的祝福。一个人活在人世间,在历史新时期之初,巴老从道义上为写真实的作品鸣锣开道,力挽狂澜,抒写出历史新时期的人文华章;到了黄昏晚年,又以铁肩担道义的无畏精神,居安思危写出一篇篇醒世箴言,其心何若美哉!其志又何其壮哉!其文字的经纬之中,蕴藏着的是一颗民族的忠魂。
巴金赠友人书
巴金晚年,对新老朋友表达友谊的重要方式之一,是签名赠送自己的近著。
1986年10月,在去杭州的列车上,祝鸿生拎着、背着巴老一家的大行李袋,他临时有事,下火车时请我帮拎一下,他说,够沉吧,衣服没有什么重量,主要是巴老带的书,多是准备送人的。
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家》新版问世,译作《往事与随想》及《巴金近作》、《随想录》等先后出版,巴老给许多人赠送书,都是自己亲自写信封,到附近邮局去挂号寄。1978年,他来北京开会,住铁道部招待所,就寄赠了《家》给我。
1979年1月中旬,我去看望臧克家,他兴冲冲地朗诵一首旧体诗《赠巴金同志》给我听,原来是他刚收到巴老从上海寄赠给他的《家》,诗云:“四十六年见故家,可怜人已老天涯。闻道纷纷还原职,为问如何复韶华?”作者附记说明:“巴金同志以新版见赠,距写作时已四十六年矣,不禁感慨系之!非绝非古,即兴成句以赠。1979年1月11日凌晨灯下。”这首诗克家初收《友声集》中。
我每次去上海看望巴老时,时有机会得到他的赐书。1982年12月30日,他送我新出的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真话集》,在飞机上我读着他在后记中末段引证了大家熟知、但未必都能领悟其意的安徒生《皇帝的新衣》的典故,他在文章中这么写道:“大家都说:‘皇帝陛下的新衣真漂亮。’只有一个孩子讲出真话来:‘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这是巴老晚年借安徒生的那则童话,留给人世的一部箴言。他坚信:“真话毕竟是存在的。讲真话也并不难。”
巴老有时让我带些书回京分别赠与老友。1988年3月,他嘱我转送一本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随想录》5卷合订本给艾青。他在书的扉页上写着:“赠艾青同志巴金八八年五月三十日。我长期患病,几年不见您了,请多保重!”艾老收到书,盯着扉页上巴老用颤抖的手写的那几句话,艾老说:这叫病人想念病人!艾老还忆起,“文革”结束后,1979年3月,他和一位诗人第一次到上海,巴金来招待所看他,并在锦江饭店请过他。1982年,他从故乡金华返京路过上海时,去巴金家看了他。以后两人相见,就多是在会议上了。
1989年,我去上海。巴老送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巴金全集》几卷给我。回京阅读时才发现,第6卷扉页上是巴老签名赠给曹禺和李玉茹夫妇的。我到北京医院看曹禺将这本《巴金全集》给他,我说可能是巴老错拿了,曹禺摆摆手风趣地说:这是老巴怕你背不动,又想让我早收到,让我高兴,只好先让你带有签名的这本来,其余的,以后到上海去拿。
巴金的力量
巴金老人百岁华诞到了,我想,华文世界的读者、作家们都会为之高兴、庆贺。
巴金生于1904年11月25日。他几乎是一位世纪同龄人。在这个充满着惊涛骇浪、诡秘风云的世纪里,巴金是这个伟大历史的积极参与者、见证者、记录者。从青年时代开始,直到九十年代后期完全病倒,他像一个战士一样,紧握手中的笔,始终写作不辍(除了“文革”时期被剥夺了做人的起码权利,当然也包括失去了写作权利)。已经出版的《巴金全集》26卷,《巴金译文集》10卷,这近千万字的译著也还不是他作品的全部。他的浩如烟海的著作是二十世纪中国重要的文化财富。
作为一位杰出的文学大师,巴金的思想和艺术魅力对于二十世纪中国读者有过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其中有两个时期可说是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冲击波。第一次,是在三四十年代,他是拥有最多青年读者群的作家。他的以《灭亡》、《家》、《爱情三部曲》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风靡一时。多少青年男女几乎是狂热地爱读他的书,以至如李健吾先生所说的那样,他们抱住他的小说,和里面的人物一起哭笑。因为他的作品不只是倾诉了他自己的悲哀,而且也表达了时代的苦闷,因而点燃了他们的心,宣泄了他们悒郁不平的感情,并使他们受到鼓舞和启示,走上了人生的新路。
第二次,是八十年代写作发表的《随想录》,这部由150篇短小杂感随想组成的书,涉及到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评估、人生价值、道德观念、文化秩序、个人思想情感等等广泛范围,形成对旧秩序、旧思想、旧文化的挑战和批判,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觉醒和痛苦的反思的结晶。它又一次点燃了人们的心,表达了各阶层潜在的或鲜明的变革要求和感受,因而被人们誉为“讲真话的大书”。他的呼唤建立“文革博物馆”,强调生命之花的盛开在于付出、奉献,以及虔诚地严苛地自我拷问和历史反思的忏悔精神,至今仍是空谷绝响,未见有新的超越。这就是巴金老人给我们的丰富的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他的伟大的人格魅力和风范仍然绵延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像这样巨大的思想艺术的冲击波,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阅读史上实在是罕见的。
少年时代的巴金,曾经梦想“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孩子的幻梦,但在巴金,却成为一生执着追求的理想。他希望的不仅是中国,而且是全人类,都能过上美好的生活。当他赴法留学途中,还曾说:“我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爱人类、爱祖国、爱人民、爱读者,使巴金成为胸襟开阔、视野深远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作家。不要以为这只是一种虚幻的空想,却是作为伟大作家必不可少的,最为重要的信念,最可宝贵的精神力量。
因此,巴金的一生和他的作品,在刚刚过去了的这个世纪显然是有杰出的代表性的。笔者深信,读解巴金,无异将是读解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和二十世纪的可歌可泣的经历,在世界历史上都堪称奇特而荒诞,严峻而悲壮,确实值得深加研究。为了使更多的海内外华人读者有机会了解这位二十世纪文学大师巴金,又值这位世纪老人百岁华诞之时,人们对此作进一步的探讨,也就更具深意了。(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冯骥才、从维熙、吴泰昌、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