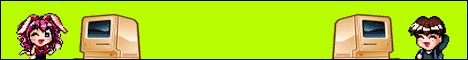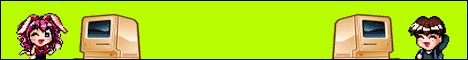(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并注明摘自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周刊》。)
当影视毫不留情地将话剧这门传统的艺术挤到边缘,话剧演员演变为影视剧最具实力的大军时,这位61岁的老人依然坚信话剧的重生,一如等待他的戈多
本刊记者/粲然
话剧《赵氏孤儿》正在北京人艺剧院演出。
10月30日晚7时许,观众们都领票进场了,在陆续传来的舞台声响中,剧院越发显出一种无法抹却的孤清。
二楼咖啡馆里,该剧导演林兆华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他穿着宽松的牛仔裤,套一件大大的毛衣。怎么看,都像个老年“哈韩族”。往来其间寥寥几个青年,都亲热地叫他“大哥”。
“我以前拍的戏,很多人说难懂。那么这次《赵氏孤儿》会让所有的人都看懂,而且觉得好看。”
《赵氏孤儿》是最早介绍到欧洲去的中国戏曲,伏尔泰进行了改写,取名叫《中国孤儿》,并把原先血腥复仇的结局改成了双方最后谅解。1990年,法国使馆的中法比较文学协会成立,委托林兆华执导该剧本,因为喜欢中国戏剧,林兆华最初用河北梆子表现这个经典剧目。北京人艺此次排演的《赵氏孤儿》是他的第二个版本。
新闻周刊:事隔13年,什么原因又让您重拾《赵氏孤儿》?
林兆华:第一,我看到京戏等几个戏曲版本,我觉得这个戏老百姓都比较熟悉。第二,一般人认为我的戏不大看得明白,但其实我的戏不是从先锋的角度出发的。我也想做一个专家们和老百姓都明白的戏。
新闻周刊:您觉得这版《赵氏孤儿》最大的变化在哪里?
林兆华:除了剧情,这个戏功夫下得最大的是表演。以往历史剧的表演方式,拿腔拿调的语言,形体上的造型,我觉得是比较虚假的。我们多年倡导的所谓主流戏剧,都是那样表现的。实际上这是对现实主义的曲解。再说得难听些,就是伪现实主义充斥舞台。我希望打掉这些东西。
新闻周刊:这次《赵氏孤儿》是否借鉴了戏曲的东西?
林兆华:我对戏曲的借鉴并不是一招一式的借鉴。中国戏曲的一大特点就是空、无。但这种“无”又包容了一切。戏曲舞台上的一切都是靠表演来表现的,这在美学上是非常可贵的东西。我喜欢戏曲的原因,就是它给我极大自由。它能做到舞台什么都没有,而仅仅靠唱、念、做、打表现出来,这对话剧导演是极有好处的。从表演的角度,坦率地说,我不喜欢演员纯体验,我喜欢感觉,演员的创作应该重“感觉”。
新闻周刊:但有人说,这版《赵氏孤儿》是“炒冷饭”,说您开始重复自己了。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林兆华:他恰恰没看懂《赵氏孤儿》。
新闻周刊:迄今为止,它的票房如何?
林兆华:票房不算太好。不比原来的《万家灯火》,场场爆满。这种历史题材的话剧,(票房)有时候八九成,有时候六七成。
“像一些古典名剧,如果硬要搬到大剧场,是打不过赵本山的小品的”
1982年,实验话剧《绝对信号》的成功,无疑是当时一统天下的传统话剧界的一声惊雷。当年看过该剧的一位观众,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幕话剧在那个年代带给自己的震动,“那天晚上我是神情恍惚地回到家的。我一直在想,原来话剧还能这么排。”
新闻周刊:您还记得刚毕业到人艺时的情形吗?
林兆华:我是1961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分配到人艺的,那是北京人艺的黄金时代。当时我对人艺排的那些好戏简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每天都有戏演,经典戏剧像《茶馆》、《蔡文姬》是排队买票。最活跃的时候,连大年三十都演戏。现在不成了。
新闻周刊:您什么时候开始单独执导话剧?
林兆华: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开始单独执导戏剧。做《绝对信号》的时候压力很大。开始我们说“这是实验话剧”,这个“实验”的意思是说,好了就上,排不好就不上。人艺提供资金,刚开始只在排练厅演,征求意见,反映挺好,才让公演。
当时小剧场在欧洲挺普遍,我们看投资的钱少,而且小剧场实验性非常强,给年轻人提供的空间大一点。
新闻周刊:压力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林兆华:那时中国戏剧千篇一律,尤其是在这个很传统的剧院做。
新闻周刊:做完《绝对信号》您就出名了?
林兆华:不能说出名,这个戏成功了,大家觉得这个导演还成,就给以后做的戏奠定了基础。《绝对信号》当时影响挺大的,全国各地(的人)都来了。一些专家原来也有两种看法。一种说,这不是人艺的传统。还有一些老专家看了,呀,还挺好看的。其实那时候演得也很简单,就是比过去说出了些新的东西,没更多的理论。但观众反响很好。一百多场,场场爆满,从1982年演到1983年。
新闻周刊:后来是不是大家一窝蜂都搞先锋戏剧去了?
林兆华:我想想,孟京辉是90年代开始搞的。但80年代的戏剧文学创作比90年代好,反映现实题材的戏剧比较多。
新闻周刊:您觉得什么原因使90年代后戏剧不好了?
林兆华:很复杂。80年代后有些作者压抑了那么多年,激情奔放了。而90年代改革开放,电视剧一进入,写戏剧剧本的人就不多了。
新闻周刊:在《万家灯火》之前,您排的话剧赚钱吗?
林兆华:我给剧院做的戏,都赚钱。我自己工作室做的,比如《哈姆雷特》、《理查三世》、《等待戈多》、《浮士德》,这些戏都不赚钱。
新闻周刊:您排这些不赚钱的剧本,是因为您觉得这些名剧应该被重温、被创新吗?
林兆华:中国到今天为止,还是强调主流戏剧。所以,你既然不排,我就拿到工作室排,自己筹集资金排。我觉得不这样做是不对的——国家剧院怎么能不演名著?像这样一些古典名剧,如果硬要搬到大剧场,是打不过赵本山的小品的,所以我在小剧场做,我只做给喜欢的人看。
新闻周刊:有人认为,独立于国家剧院之外,戏剧工作室的出现更多地是为个人谋取利益。
林兆华:他们赚钱有什么不好?孟京辉的戏吸引很多年轻人,有什么不好?有人批评他。但我说,孟太少了,应该多一点。现在有很多骂他们的话,我不明白骂人的那些人的心理。他们真懂得戏吗?有些评论家,只要是贴近主旋律的戏,不管多臭,都可以吹捧。而对孟京辉、李六乙那些年轻的导演做的尝试,怎么就那么刻薄。
当然也有各种原因对戏剧环境的污染,比方过分强调商业化。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中国的(戏剧)制作人还是初级阶段,并没有把制作戏剧放在文化艺术角度做,从商业角度考虑得更多一些。尽管这样,独立工作室的出现也是好的。
“戏剧永远不会死。我们把戏剧人才圈在戏剧圈内,是非常愚蠢的事”
近十多年来,林兆华的每部戏,都会引来媒体关注的目光。我们无法判断媒体和观众的关注对林兆华个人创作的风格有多大影响。但是,可以看到,林兆华自己多年来的创作轨迹,非常切合于媒体和观众趣味的不断变化。
新闻周刊:这么多年来,哪部戏可以称得上您的代表作?
林兆华:《哈姆雷特》吧,《等待戈多》、《理查三世》都不错,还有《风月无边》那个舞台。《万家灯火》不成,那不是传世的东西,是大众通俗戏。
新闻周刊:在业内有一种说法,比如孟京辉,他一直树立实验的先锋的旗帜,但看您的戏剧,却觉得时而非常实验,时而非常主流。为什么您要这样做?
林兆华:也不全是,比如《红白喜事》,实在得要命,舞台上烟可以冒烟,井可以打出水来。我都是根据戏的需要做的。
新闻周刊:《万家灯火》热演时,有人指出,话剧圈有两类铁杆观众,一类是热衷传统剧目的中老年人,一类是部分青年白领。但前者认为您的戏晦涩难懂,后者认为您的戏不够时尚。两部分观众都背离了您,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林兆华:我就是中庸。中庸之道是非常舒服的。大师的戏我也看过,理论家的书我也看过,但我不按照专家说怎么做,或者一个流派说该怎么做去做。我有自己的认识,我要创造(我的)学术和流派。
新闻周刊:熟悉您的人说您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断地创新”,您是否因为创新而创新,有搞噱头之嫌?
林兆华:原来很多教授对我也有一些意见,说我搞形式。我认为这是他们没形式,所以说我搞形式。可艺术形式是一个艺术品成熟的标志。我们原来只强调戏剧的内容,但怎么可能形式离开内容呢?真正的艺术品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结合,我们过去就是只强调意识形态,不强调艺术形式。
新闻周刊:您到这么大年纪还在一直创新,是否担心创造力枯竭的时候?
林兆华:我不担心。我脸皮比较厚,我做戏没有负担。我每当做一个戏,不考虑失败如何,成功如何。我想做就做了。
新闻周刊:做那么多年话剧,您觉得最无奈的是什么?
林兆华:其实我想说,我觉得无奈的,不是票房,而是体制。中国戏剧体制,早已落伍了。我们有些戏并不比发达国家差,但戏剧状态还是不行。
新闻周刊:如果体制打开了,观众还会回到戏剧中来吗?
林兆华:戏剧永远不会死,永远不会死。我们把戏剧人才圈在戏剧圈内,是非常愚蠢的事。应该让尽量多的人进来。-
林兆华
了解林兆华,等于了解了上世纪60年代至今的中国话剧史。
1961年,刚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的林兆华,被分配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那年他19岁。
1982年,政策甫一放开,当年“怀着对经典名著五体投地的心情”进入人艺的他,率先发动了当代话剧史上第一场“造反”:执导了第一场先锋实验话剧《绝对信号》,并获得巨大成功。中国小剧场话剧的演出形式也由此开始。随后他又导演了《车站》、《野人》等实验性话剧,同样反响强烈。
1985年,当“实验”之风逐渐在中国话剧界盛起之时,林兆华却排演了现实主义题材的话剧《狗儿爷涅》。而接下来他导演的《哈姆雷特》、《浮士德》及《等待戈多》等话剧,似乎又在向人展示其驾御国外经典的“功夫”。
有人称他为“中国话剧史上最重要、最具革命性的导演”,而其不断在先锋与现实话剧之间游走的风格,一方面被认为是他驾御不同话剧题材功力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使他陷入既不俗又无雅的尴尬角色之中。
近日由他执导,正在北京人艺上演的《赵氏孤儿》,因为濮存昕、徐帆等名角的加入,也颇受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