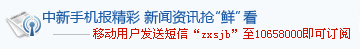《中华文摘》文章:“文革”中的曹禺
(声明:刊用中国《中华文摘》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文/梁秉堃
曹禺师曾经对青年学生说过这样的话——
“我一生都有这样的感觉,人这个东西是非常复杂的,人又是非常宝贵的。人啊,还是极应当把他搞清楚的。无论做学问,做什么事情,如果把人搞不清楚,也看不明白,这终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笔者有幸在曹禺师身边工作、学习42年之久,耳提面命受益匪浅。这些年经历的许多事情当中,有些是很难忘怀的。
总是写不好“认罪检查”
大约是在1973年下半年,“毛泽东思想解放军宣传队”和“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一起进驻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理直气壮地声称要代表无产阶级占领这个已经被资产阶级统治多年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桥头堡”。当时有一副写给剧院的对联,上联是“庙小妖风大”,下联是“池浅王八多”,横批是“彻底砸烂”。
很快,在北京人艺院长曹禺师住宅的大门上,也贴了一条大标语——
“打倒反动权威、反革命文人曹禺!”
当时根据上级的指示,要“解放干部”,让曹禺师“认罪检查”以后,回到“革命群众”当中去。也就是说,他必须写出一个像样的、深刻的、上纲上线的认罪检查,才能获得“解放”。对此,曹禺师被特别批准不参加劳动,埋下头来专门写“认罪检查”报告。万万没有想到,报告竟然被“军宣队”政委一次又一次以“认识不深刻”和“根本没有上纲上线”为由打了回来,命令重新再写。接下来,一而再、再而三地写,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打了回来。曹禺师压力很大,苦不堪言,经常坐在小马扎上,一言不发,两只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白色的墙壁,似乎是在望着自己波澜起伏的内心。
那时,剧院已经全部改为部队编制,我和曹禺师刚好在一个班里,我由于年纪较轻、历史简单当上了班长,所以很快就发现他那忧心如焚的可怜样子。为此,我心里也很不安,可是,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办才好。而且,“军工宣队”还催促得很紧,要求必须尽快交出“认罪检查”报告来。一天中午,曹禺师急得连饭也没有吃,坐在房间里通铺前的小马扎上,再次两只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白色的墙壁,手里拿着纸和笔,唉声叹气,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我走了过去,没有吭声。他突然忍不住轻声对我说:“我就是孙子!也不是孙子,就是一条虫,随他们怎么碾!”我看着这种情况,拍了拍他的手。不知道为什么,灵机一动,想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来,赶忙悄悄对他说:“干脆,我帮助您写吧。”曹禺师大吃一惊,立即向周围看了看,唯恐被什么人听见。我又向他点点头,表示只好如此。曹禺师胆战心惊地问:“这样能行吗?”我说:“先交出报告过了关再说……反正就是咱们两个人知道。”
我怎么会有几分把握代写报告呢?因为我已经逐渐揣摩出“军宣队”政委的想法,那就是必须把自己狠狠地臭骂一顿,再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纲”、“线”上得高高的、满满的,那就可以被叫做“认罪检查”很深刻,对无产阶级专政有感情,和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了。否则,你交待和分析得再彻底、再中肯、再有道理也都是无济于事的。
对于代写“认罪检查”报告,曹禺师当然求之不得。但是,也生怕暴露出去惹来更大的麻烦。为此,我们讲好一定要严格保守秘密,要“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等我写好以后,他抄一遍再送上去。接下来,我就偷偷地开始动笔了。在代写的过程中,我发现资料不齐全,很是影响进度。譬如说,“造反派”的人揭发曹禺师过去曾经在报纸上写过一篇文章,极力要求提高文艺作品的稿酬标准,必须深刻检查,狠挖“三名三高”的反动名利思想。据说,这篇发表的文章在抄家时被拿走了,因此“认罪检查”就没有了充分的依据。我赶紧问曹禺师还能不能找到原文或者底稿,他含含糊糊地说不大好找了,只能作罢。没想到的是,从此以后,曹禺师几乎每次休假从家里回来,都能背诵出文章的一两段。开始,我并没有留意,后来他背诵得太具体了、太顺畅了,几乎一个字都不错,这就让人产生了怀疑。我问:“您是不是在家里还有一份文章的底稿啊?”他突然脸色发白,一下子愣住了,想了半天,才不好意思地喃喃道:“我是还有一份文章的底稿,就藏在方瑞(曹禺师夫人)的小皮箱子里,可真怕他们再来抄家,要是再给抄走了,我写的是什么就真的说不清楚了。死无对证,死无对证啊!……可怕!真是可怕!什么都可怕!”我想,这是曹禺师胆子本来就小,后来又让抄家、批斗给搞怕了。我面对他那痛苦之极的脸,真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心里暗暗想着:“一个正直、善良又诚恳、纯真的人,怎么可以硬是把灵魂给扭曲成这么一个样子了呢?”下一次休假从家里回来,曹禺师就把文章的完整底稿悄悄交给了我,还一再嘱咐我务必妥为保存,千万不要丢失。我立即连连点头,完全答应下来。
在这段时间里,曹禺师的心情似乎是逐渐有所好转的,因为毕竟是“干部解放”已经有望了。记得,剧院有一位曾经在抗战时期“江安”剧专做过他学生的,并且是很有成就的女演员,当时的处境十分困难——自己不到年龄就被强迫“退休”,丈夫在山西劳动改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身边只有一个正在上小学的孩子。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位演员对于生活完全失去了信心,准备找个地方一死了之。曹禺师得知这个情况以后,马上给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上说:“雄心不取决于年岁,正如同青春不限于黑夜,也不忍随着白发而消失。”女演员含着眼泪读完这封信,从此打消了轻生的念头,并且,拿起笔来,断断续续写了散文、报道、回忆等等几十篇文章,发表在报刊上。这些就成了她的精神寄托。曹禺师知道这一切以后,随口说出:“我真是很快活啊!”
由我代笔的“认罪检查”报告很快就出来了,里面基本上都是采用“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中的社论语言。曹禺师看了以后,仿佛还有些顾虑,欲言又止。譬如,报告里必须承认自己是“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他总觉得承认了“反革命”三个字,就是承认了自己是美帝国主义分子、苏联修正主义分子和国民党特务分子,那可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这样检查根本就过不了关。通过我的一再解释,他总算是勉强接受了,同意拿回家里重抄一遍。
“认罪检查”报告送上去以后,“军宣队”政委表示还可以,没有再打回来。在我们等候上级批复的时候,竟然没有了下文,或许是上边什么人从中作梗又说了坏话,曹禺师的“干部解放”问题,便成了“可以解放但还定不下来”的特殊状态,硬是给拖了下去。
这样,曹禺师本来已经好转的心情,又一落千丈,重新恢复到方瑞师母刚刚去世时的情形。那时,他整日里欲哭无泪,仿佛眼泪已经流尽。他怎么也想不到妻子会这样凄凉、悲伤、孤独地死去。他知道,妻子为了自己和孩子受了多少苦难。他知道,方瑞师母把青春、爱情、心血和生命全部献给了自己,如同《北京人》里的愫方——这个善良、正直、生动、可爱,使人难以忘怀的戏剧人物,曹禺师就是以方瑞师母为原型写出来的——那样,“把好的送给别人,把坏的留给自己”。在“文革”中,方瑞师母用衰弱的身体,不声不响地支撑着自己的丈夫,把所有的痛苦都埋在心底,并且鼓励他度过最难熬、最凶险的日子。
就在这个时候,“军工宣队”带领我们全体“革命群众”和“牛棚”里的“一小撮”“革命对象”,都下放到南口林场,一边继续搞运动,一边参加劳动。
在我们给苹果树“扩坑”的劳动当中,曹禺师笨手笨脚地被一根杉篙碰破了头皮,幸好不太重,只在医务所缝了几针。受伤以后,他躺在宿舍里休息。一天,“军宣队”政委来到班里,我们以为是来表扬一下,起码是来慰问一下,谁想到他竟然当众对曹禺师说道:“曹禺啊,你光碰脑袋外边儿可不行,要狠狠地碰里边儿,那才叫‘灵魂深处闹革命’嘛!”面对着这样一句既不讲理,又不讲情的话,曹禺师虽然表面上笑着,点头称是,实际上却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很快,他又变成一个长时间“面壁”的“无言者”了,似乎是望着自己活生生的痛苦沉思。正如他说的:“天沉着脸,像是又要下雪,其实方才还是亮晶晶的,怎能一转眼就变成一副讨人嫌厌的样子。这个天就像我,一天能几个神气,说明心中有怨气。……我是人,人却不能不有各种变化。譬如我总像在等待什么,其实我什么也不等待。”
传达室看门人
后来,曹禺师由于受到长期折磨,心力交瘁,难以支撑,不得不住进了协和医院。从医院出来不久,他被送到首都剧场传达室,也就是北京人艺传达室去“看大门”。这是与“关牛棚”不同形式的另一种惩罚。每天管分发报纸、信件,办理来客登记手续,同时,还要负责打扫整个剧院的大院子。后来,由于日本话剧团要来演出,怕被外宾发现给“国外阶级敌人”提供“反面宣传材料”,才把曹禺师转移到史家胡同56号北京人艺家属宿舍的传达室去“看大门”,除去在剧场的原有工作,还增加了给家属传呼电话和倒垃圾的任务。他头上戴着一顶蓝布旧帽子,脖子上系着一条白毛巾,上身是已经不干净的白背心,下身是一条肥大的短裤,脸上乐呵呵的,干得很投入,很卖力。他整天干这干那,跑前跑后,喊来喊去,累得满头、满身大汗淋淋,说什么也不肯稍微喘上一口气,休息休息。
一天,曹禺师在清晨走出家属宿舍大门扫地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东边一条小胡同口上,站着一位老年妇女。起初他什么都没想。第二天他发现那位妇女又来了,还是一动不动站在那里,一直都是面向着自己这边看个不停。第三天、第四天都是如此。到第五天的时候,曹禺师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在出门扫地的时候有意放慢了节奏,注意向着那个妇女的方向看去,发现她还在眼睁睁地注视着自己。可惜,由于天刚蒙蒙亮,路灯已灭,自己又是个大近视眼,根本没看清楚对方的模样。一天清晨,曹禺师边扫地边大胆向那位妇女靠近,越来越近,终于看清楚了:原来是十多年以前由于性格各异、感情不和而离婚的前妻郑秀女士。实在是太意想不到了。
曹禺师与郑秀早在1950年就离婚了,“文革”开始以后,郑秀一直通过两个女儿打听他的消息,心想,也许能与他见上一面。郑秀觉得此时此刻完全应该出现在前夫的面前,这样也许会使对方心里多少感到一些安慰和支持。可是,曹禺师心里想的却是,千万不要因为自己而拖累他人,也包括郑秀在内。于是,这时一种感激之情、歉疚之情便油然而生。他多么想走上前去说上几句话啊,可是两条腿无论如何也迈不开步,深怕自己给对方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而郑秀何尝不想走上去说几句话、问一声好呢,可她同样没有迈开脚步,深怕自己给对方增加什么“罪状”。他们佯装是面对着陌生人,默默地对视了许久,脸上没有任何特别的表情。然后,曹禺师急匆匆转身扫起地来,很快就走进了家属宿舍大院。郑秀走进东边那条小胡同里,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从此以后,郑秀再也没有来看过曹禺师。写到这里,我想起万方述说老爸的一段话:“他骨子里实在是一个太真诚的人,心里的快活和悲哀像地下的泉水一样,有一点点压力就止不住一股股地冒出来。想来那没有别的原因,那是一种自然现象。想到他的这份天性,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难过极了。”我完全赞成万方的观察和理解,甚至连她的“难过”我都表示认同。
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
后来,曹禺师口头上少言寡语,行动上老老实实,可以说更加不敢越雷池一步。为此曾经受到市革委会领导的当众表扬,说“曹禺改造得还不错”。具体理由是——他每天中午在食堂只吃半个窝头和五分钱一碗的熬白菜,装在一个大茶缸子里捣碎,不坐在座位上,而是站在门边很快吃完。同时,他只吸一毛钱一包的劣质烟,一吸就“放炮”,还咳嗽不止。
然而,曹禺师灵魂深处厚重的痛苦,是明眼人完全能够看到的。实际上,如他在诗中所说,他的境况是,“孤单,寂寞,跌落在深血弥漫的地狱”。
众所周知,曹禺师早在23岁的时候,因写出《雷雨》而一举成名,25岁的时候,又因为写了《日出》,而被赞誉为“摄魂者”。可以说,他是中国话剧史上的一代宗师。然而,他的卓越成就,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完全被抹杀了。当时,曹禺师不但逢人——不管老人、中年人还是小孩子——都要深深地弯下腰去,鞠一个90度大躬,再大声说一句:“我是反动文人曹禺!”而且,在内心里认为——相当真诚地认为,自己从来就不应该写戏,不应该毒害观众,就连自己走到这个世界上来都是完全多余的。
曹禺师想到——
自己一生写过那么多剧本,居然没有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
自己写《雷雨》是要干什么?还不是为了宣传反动的、毒害人民的“宿命论”?
自己写《日出》为什么不写共产党的诞生?只有共产党的出现才是真正的日出啊;
自己写《北京人》其实就是为那些腐朽的、没落的遗老遗少大唱挽歌;
自己写《原野》是在写一个年轻农民,一种莫名其妙的、盲目的复仇主义的思想感情。
……
现在的人是无法想象的,曹禺师甚至常常独自一人站在毛主席彩色画像前,无限忏悔地流着眼泪说:“毛主席啊,我的罪孽深重。我要老老实实向您请罪!向人民群众请罪!”甚至跪在地上,请求方瑞说:“你就帮助我死了吧!”
一直到“文革”结束后,曹禺师在接受记者赵浩生采访时,才把心中的秘密和盘托出。“我的遭遇还算好的。被关了几年,后来又劳动。劳动本来是很好的事,如果把劳动当成惩罚、侮辱,那就不太好了。不只要劳动,而且跟家里隔离,甚至影响到孩子,一直搞得你神志不清,最后甚至会自己也觉得自己不对。因为他们成天逼你念叨着:我是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
赵浩生问:“您的最大罪状是什么呢?”
“反动呀!反动文人,反动权威,30年代文艺黑线,腐蚀了许多年轻人……真难说,我们写的东西最初出现的时候,还有人说过我们进步。他们逼着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连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造成自卑感,觉得自己犯了大错误,不要写戏了,情愿去扫街。这种自暴自弃的思想就产生了,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
一直到了1978年6月30日,北京市文化局才正式发出文件,为曹禺师平反落实政策,恢复了他在北京人艺的院长职务。
14年前的冬日,曹禺师辞世了。遗体告别的那一天,最后等待取走骨灰的时候,他的子女们坐在殡仪馆院子里的空地上,望着蓝天白云。日上中天,几只喜鹊叫着飞来飞去,烟囱里飘出淡淡的灰烟,大家不约而同地感觉到,这就是曹禺师的身影。有人说:那灰烟会飘落到地上,等到春天的时候,草长出来,花开了,他也就在那些生命里边了。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参与互动(0) 参与互动(0) |
【编辑:杨彦宇】 |
-
----- 精选 -----
Copyright ©1999-2024 chinanews.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