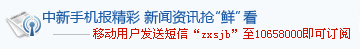青戏节艺术总监回应质疑 孟京辉:人多玩戏才能火

青戏节艺术总监回应质疑
孟京辉:人多玩戏才能火
孟京辉这几年变化很大。变得温柔了,也变得可爱了。如果你问他是不是这样,他会歪着脖子托起下巴想一下,然后说“好像是”。与同在创作高峰期的中青年导演不同,孟京辉如今对自己的定位似乎并非只在于艺术创作本身,从最初亲历拉赞助排戏,到后来开剧场自己当老板,再到当前,由他担任艺术总监的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飞速走到了第三届。一位艺术家如果不能纯粹于艺术本身,就会有许多的质疑之声,于是一些观众便认为孟京辉已经到了创作匮乏期,甚至有人直言他是在“吃老本”。这些质疑要在过去,孟京辉或许会愤怒地回击,不过现在的他却非常清醒。他告诉记者,外界的质疑只是片面的看法,而他从上学时就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戏剧一定需要很多人一起来玩才够热闹,所以他会很高调地去张罗各种与戏剧有关的事。
谈青戏节
要让小剧场形成爆炸期
新京报:北京青年戏剧节(以下简称青戏节)又开幕了。听说你这个艺术总监还身兼数职,不仅把关作品,还要拉赞助、做推广。
孟京辉:三年前我发起做青戏节的时候,就觉得北京是个很有创造力、资源丰沛的地方,创作空间和各种趋势都越来越好。尤其今年上升到国际领域,我非常高兴。在我看来,艺术总监在青戏节的工作,就是要推动所有的事。首先我要从政府部门和各种相关的基金会那里找钱;其次我要把握戏剧节的组织形式;第三在艺术上,寻求独特性和多元化的作品。青戏节是有公益性质的戏剧活动,我希望这里崇尚一种自由的,形式感突出的,实验性的和互动性的创作。所以我必须干乱七八糟好多事,甚至于戏剧节形象标识、宣传册也要管。
新京报:青戏节的白色斑马标志在今年变成了彩色,以后怎么办?
孟京辉:三十多出戏,我有朋友就抱怨看不过来,我说也许我拉个A套餐、B套餐之类的,这样就满足不同观众的需求了。记得三年前刚开始提出青戏节的概念时,还只是一个梦想,或者没奢望能有几十部戏,可是三年后真的做到了,我很自豪。我想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做下去,等到第四、第五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总结经验、教训了。好多人也问我,你没事不好好做戏,搞什么戏剧节啊。可是我爱热闹,尤其在一个月中能让北京的小剧场舞台形成爆炸期,这多来劲儿。
新京报:听说你不喜欢偏商业的戏剧,或者有商业投入的戏剧纳入戏剧节。
孟京辉:是的。青戏节的资金大约一半来自政府,30%左右来自基金会。还有30%来自之后的票房。我们资助的是有想法、有创意的年轻人。特别商业的戏是对公共资源的一种不公平的运用。与国外各种戏剧节相比,我们的投入和规模相对还很初级。怎么能做的好,同时又能在当前的文化条件下做的恰当,这并不容易,得慢慢摸索。
谈创作
继承传统是败家子的说法
新京报:谈谈你去国外的一些感受吧,这两年老出去看戏,是去充电了吗?
孟京辉:这两年我确实比前几年出去得多。去纽约,去伦敦,去柏林,还去法国、意大利等等。这是瞎玩,去感受一下气氛。其实欧洲的戏剧节,我很早就开始参加了,比如比利时实验戏剧节,还有《等待戈多》去德国演出。我对欧洲的戏剧情有独钟。不过这几年我自己的戏没出国。第一怕麻烦,第二我认为外国人看不懂。最重要的是我没有一个国际语言来跟他们对话。在国际的大背景下说作品,到底是自说自话,还是这些东西确实值得在国际范畴里倾听,这个事情我搞不清楚。
不过今年我去法国阿维农戏剧节,却有了一个蠢蠢欲动的感觉。我发现如今可以不再穿长袍马褂,不用掏出老祖宗的玩意就能和这些老外交往了。因为他们和以前不一样了,平和了,可以用一个非陌生化的观点和非激进的态度来面对中国文化了。这让我感觉戏剧交流,此时此刻变得有空间了。
新京报:你为什么没想到做一个经典作品的中国式表达,这样外国人知道剧情,也可以交流吗?
孟京辉:我反对愚蠢的和那种不自由的创作思想,希望能创造一种新的形式感,一个新的表达。当然了,也有人说,孟京辉算什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他不是外国人说的“中国的”。可是,中国的戏曲,中国的美对待传统,我认为必须要超越,继承传统是最败家子的说法。因为你流的血,你每天的成长氛围、生活环境、处事方法,得到的痛苦,得到的对信仰的迷恋,都是财富。怎么这些东西都不说,偏说家里压箱底的那点东西?
以后有“青戏节一代”
谈理想
新京报:你现在全部精力都在青戏节,接下来的创作怎么办?
孟京辉:其实所有事都是按部就班进行的,我们有详细的计划表。比如这两个月的精力我都给了青戏节,我的制作人在上海操作我工作室的事。但青戏节一旦推上轨道,我的状态就转移了。我会选择看自己感兴趣的戏,和年轻的创作者们讨论想法。一方面可以丰富我自己的感受,另一方面我有时间静下来想想接下来要做的事。今年11月,和明年上半年我都有排新戏的计划,包括明年下半年我也准备排一部大型的音乐剧和一部话剧。
新京报:看来你分身有术,而且开心事多过烦心事。这是如何做到的?
孟京辉:之所以既能做很多事,也能做自己的作品,正是因为这些年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模式,就是连演和巡回,同时拥有自己的签约演员,还有新剧本的开发。大家都说剧本荒,可我们却多得是。唯一的问题是,在现阶段这种大环境下,我们对世界优秀剧目的推荐还有欠缺。
新京报:没人敢排,因为不够商业吗?所以你也不敢。
孟京辉:确实因为商业的问题。英国、法国、德国,他们就会演契诃夫的戏,演莎士比亚的戏。他们知道这是戏剧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我们却很可怜,除了学校会在毕业大戏中排一些这类的作品外,它和社会的递接是缺失的。我们这次青戏节的戏有向大师致敬的单元,但也仅仅在这里(才有)。当有朋友问我,孟京辉你不是超喜欢契诃夫,不是认为自己很牛,号称很能控制自己,控制社会审美吗,为什么不敢排呢?一句话让我汗颜。我也会问自己到底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可是让我排《哈姆雷特》,我还是不敢。林兆华导演敢排《哈姆雷特》,他勇敢地走出了这一步也是有很多资源来配合他,他是假借勇敢来面对整个环境。所以现在我也在不断总结,在对自己出现的问题的认识过程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实际上这些事不归我来做,可我觉得我有职责。
新京报:你策划北京青戏节,从自私的角度来说,是不是也希望通过了解更多年轻人的想法,激发自己的创作?
孟京辉:这个倒不需要。我也是形式主义比较严重的人,每年会到国外看各种各样的戏。如果非要说一个最自私的想法,那就是:戏剧必须要有更多人玩才能红火。这是我早在中戏上学时就感受到的。当时我就和院长徐晓钟说过,希望他能留几个像我们这样的毕业生,每年让一些人来做戏。当时我们只能建议学校来做。不过现在条件好了,我自己可以做了。我一直有一个八十年代的傻逼理想,想建立理想的戏剧环境,给后面的人提供温床,这是一种自恋的感觉。我认为若干年后,肯定会出现一个词,叫“青戏节一代”。
找到了商业和自我的平衡点
谈市场
新京报:你在题材选择上偏重市场需要的东西,比如情感题材。你觉得在商业性和艺术性之间,如何找到平衡点?
孟京辉:我找到了不用理睬商业性,也不用理睬自我表达的个人特点。这中间混合了好多可能性,我让它自己运作,自生自灭。比如向《恋爱的犀牛》和《两只狗的生活意见》,一个特别情感,一个特别社会,就像两个小部队;另外,我也想做一些所谓实验性(作品),比如《爱比死更冷酷》;还有,就是在一个非主旋律的情况下,形式和内容都特别独特,又能直接和某种思想对位的戏。前些天我和廖一梅看了昆汀·塔伦蒂诺的《无耻混蛋》。把我俩惊着了。他在现在这种主流意识下,居然能做出一部跟所有人没关系,却能直指人心的作品。那么我呢?上帝还赋予我一点才华,所以我在找这种东西。一个跟我自己能特别联络,并不完全跟别人同等的自我抒发。
新京报:像你前两年说的最有名的话,“大众审美是狗屎”,现在还这么说吗?
孟京辉:当然了,这肯定的。举个例子,几年前我家请了一个小阿姨,她的爱情很不顺,总是哭,有一次我们问她哭什么,她拿着手机里的短信给我们看。这一看我才知道,原来她和对方短信里写的都是电视剧里那些话。这些东西,就是建立在整个传媒和平台上的大众审美,那当然是狗屎了。
新京报:你的作品,一直以来都很少见大团圆的喜剧结局,悲观的东西一直都存在,这是为什么?
孟京辉:其实最悲观的是廖一梅,她是从头到尾悲观。我是从头到尾乐观,等到最后一瞬间,我自己跟观众一块难受。这种难受会被迷恋的,就像迷恋一种回忆,一种人和人之间时间的错位等,而且不会清浅。包括《三个橘子》的结尾,我也可以有好多种结尾,但是我选择了一种最没希望但另一方又点燃希望的矛盾结尾。我喜欢这种带有不确定性的感觉。
新京报:这些年因为你一直游走于商业戏剧中,所以也会有很多争议,比如一些人觉得这几年,孟京辉还是在吃老本,或者质疑你的创作是不是出现瓶颈。你觉得呢?
孟京辉:因为不容易。他们说的有他们的道理,可是站的角度不同。在我看来我现在和吃老本没关系,因为我很早就把后院的百宝箱都扔了,哪里有本呢?另外瓶颈也谈不上,我现在井喷还不够呢。
记者 天蓝
 参与互动(0) 参与互动(0) |
【编辑:张中江】 |
Copyright ©1999-2025 chinanews.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