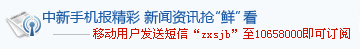雅俗标准如何辨析?今天应反对的“三俗”是什么
党中央和各级政府首先应该有一双“万山大叔的眼睛”,带领人民认清何为雅、谁是俗?方向搞错了,就会导致亲者痛、仇者快的严重后果
什么是雅、什么是俗
究竟什么是“庸俗、低俗、媚俗”?社会各界存在着不同的认识。这些认识之间的差别,甚至可以大到完全相反。笔者研究雅俗文化问题将近20年,当年的博士论文就是探讨抗战期间中国文学“超越雅俗”的课题。学术界已有的认知,“雅”和“俗”本来没有褒贬色彩,只是类别上的不同。“雅”本来是“夏”,指的是周王朝统治的核心地区,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文化中心地区”。而“俗”指的是其他地区。我们不能说非文化中心地区的文化,就比中心地区“低下”,正像今天不能说一个四川人、广东人、东北人,就不如北京人有文化。根据著名美学家、《民国通俗小说论稿》的作者张赣生的研究,中国人产生“俗”这个概念,大约是在西周时代。殷商的甲骨文和铜器铭文中均未见有“俗”字。到西周恭王(前968—前942)时所作卫鼎和永盂的铭文中已有“俗”字,用于人名;宣王(前827—前782)时意指礼法,已具“风俗”的意思;同时代的毛公鼎铭文中的“俗”则当作“欲”解。西周铜器铭文并不常见“俗”字,现知仅数例,用法大体如此。从传世古籍来看,《易》、《诗》、《书》、《左传》和《论语》等重要典籍中均未见“俗”字,这不会是偶然现象,它似乎证明“俗”的观念在春秋时代尚未得到普遍确认。
进入战国时代以后,“俗”成了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如《孟子》云:“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庄子》云:“差其时,逆其俗者,谓之篡夫;当其时,顺其俗者,谓之义之徒”,《管子》云:“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不明于化,而欲变俗易教,犹朝揉轮而夕欲乘车”,《周礼》云:“以俗教安,则民不愉,”《礼记》云:“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如此等等指的都是风俗或民俗,即某一民族或地区由习惯形成的特定生活方式。风俗之“俗”本无所谓褒贬意,故《荀子》云:“无国而不有美俗,无国而不有恶俗。”风俗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文化现象,它不是个人有意或无意的创作,而是社会的、集体的现象,是一种非个性的、类型的、模式的现象,它体现在一般人的生活中,由此又引申出“俗”的另一层含义——“世俗”,在“俗”字前加上“世”字,是指一般情况,虽然含有“平凡”的意思,但并不一定就是“俗不可耐”,如《老子》云:“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墨子》云:“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都是指一般的见识不高明而已。
所以,我们今天的人应该知道,“俗”是一个双重语义的概念。当它作名词时,是习俗、风气,“多数人普遍实行的习惯生活方式。”当它作形容词,表示性质、特征时,则是凡庸。这两重语义经常是同时呈现、含混表达的,如钱钟书阐述汉字中蕴含的辩证法时所云:“赅众理而约为一字,并行或歧出之分训得以同时合训焉,使不倍者交协、相反者互成,……语出以关,文蕴两意,乃诙谐之惯事,固辞章所优为,义理亦有之。”笔者认为,世界上一切伟大的文化,都是“通俗文化”。正如老舍先生指出的,“俗而有力”,就是伟大。荷马史诗、诗经楚辞、格萨尔王、唐诗宋词元曲明说……直到五四白话文和诸多“红色经典”,都是“通俗”的。
“通俗”有两种意思,“与世俗沟通”和“浅显易懂”。我们必须从两方面来理解,才能把握通俗文化的本质。“与世俗沟通”强调的是创作精神,“浅显易懂”强调的是审美品位。两方面既相区别又相依存,“沟通”才能“易懂”,“易懂”才能“沟通”。人们的理解多偏重于某一面,才产生了许多误解。
所以,“俗”不等于庸俗、低俗、媚俗。大俗就是大雅,例如白居易、红楼梦、赵树理、老舍、巴尔扎克、披头士等。而故作高雅,反而恰恰是一种“恶俗”。“媚雅”与“媚俗”,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通俗”类别的文化产品中,可以有“大雅”出现,就像《诗经》中包含着“风雅颂”一样。而所谓“阳春白雪”的类别中,也产生着大量的垃圾。例如我们不能说每一首交响乐都是“高雅”的,千千万万的交响乐、朦胧诗、文言文里,包含着大量的仿制品、劣质品和心理不健康的作品。而相声、快板书、评弹、摇滚乐、乡村音乐这些“通俗”的类别中,却可以产生流芳百世的经典。
 参与互动(0) 参与互动(0) |
【编辑:张中江】 |
Copyright ©1999-2024 chinanews.com. All Rights Reserved